近日,读到李春阳的文章“《人民画报》:(1950–1966) 美术作品的“革命性叙事”语言”(以下简称为“《人民画报》的‘革命性叙事’语言”),颇受启发。在此,谨以围绕历史、语言、时代反响的三点体会与各位读者分享。
人民生活现场的视觉档案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从未间断出版的四大报刊之一,《人民画报》为我们提供了记录当时人民生活现场的珍贵视觉材料。李春阳选取了其中带有时代生活气息同时反映历史意义的美术作品进行解读。
例如,武金陵插图《建设咱们的新中国》中,普通工人形象代表新中国初期生产劳动的典型符号;崔家声的科学家插图记录了当时“科技救国” 的集体渴望;邵宇《毛主席和劳动英雄们》则以温暖柔和的色调打破传统绘画的等级界限,让领袖与群众在同一光源下展露微笑,消解了身份差异带来的距离感。
“人民性”是这一时期画报美术作品的核心维度,也是李春阳关注的重点。《童年》用粗粝却充满力量的线条勾勒孩童的布衫褶皱,明亮色块在黑白版画中晕染出对未来的希望;《庆丰收》里,多个人物与多头牲畜构成充满烟火气的丰收图景,解放军战士帮农民搬运玉米的身影,成为“军民鱼水情”最生动的视觉注脚。李春阳留意到,这些美术作品构建出比文字档案更鲜活、更具情感温度的时代图景,让历史中的“人民”形象从概念变为有血有肉的视觉图像。
这一视觉转化的过程不仅是对社会现实的艺术写照,也是一种“符号建构”。正如罗兰·巴特所言,视觉图像常常承载超越表层意义的“神话”功能。置于文艺作品“人民性”的探讨中可以发现,工人、农民、战士等这些“人民”形象并非单纯的写实记录,而是通过符号的再生产将劳动者的形象转化为国家叙事中的象征符号,从而形成一种跨越个体经验的集体象征。
革命性叙事的艺术语言
李春阳此文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分析这些作品如何构建“革命性叙事”的艺术语言,它们模糊了传统意义上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的界限,更重视背后的革命精神。例如,《红军过雪山》,通过倾斜的地平线制造出雪山的压迫感,而战士们的剪影则连成一条向上的斜线,形成“压迫与抗争”的视觉张力,暗喻 革命必胜”的信念;《飞夺泸定桥》以桥梁的横构图切割画面,摇晃的锁链成为视觉焦点,扭曲的笔触则强化了河水的湍急,让“飞夺”的惊险与革命勇气跃然纸上。《风雷》则延续了“以形载道”的传统,通过人物迎风站立的姿态,既展现了自然景象的磅礴,更隐喻了革命时代的激情与力量。李春阳指出,“革命性叙事”的艺术语言主要为了突出典型人物、事件,采用宏大叙事的表现形式,以写实为主,同时与中国传统美术的写实有重要区分。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这类视觉表现实际上是一种“情节化”过程。海登·怀特提出,历史事件只有在被编织进特定叙事结构时才具备意义。这些美术作品通过将“压迫—抗争—胜利”塑造为一种经典的视觉母题,确立了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并在艺术层面完成了对国家与主流意识形态正当性的象征性确认。
李春阳以《人民画报》美术作品为对象,关于“革命性叙事”艺术语言的分析对于革命题材作品的研究颇有启发。因为革命题材作品的叙事密码不在于孤立的图像元素,而在于符号间的结构性关联与时代话语的隐性耦合,他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参照。任何时代的政治艺术都存在“显性话语——隐性符号——接受心理’的转化链条,这一思路不仅适用于新中国美术研究,也适用于其它政治美术作品研究,推动相关研究从感性认知走向理性化、系统化的方法论建构。
穿越时空的群众共鸣
笔者着笔之时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站在当下的历史节点回望过去的经典作品,“《人民画报》的‘革命性叙事’语言”对于革命性美术作品的关注有高度的时代意识与历史意识,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是激活集体记忆、凝聚民族精神的纽带。例如,《过水草地》没有聚焦领袖或英雄,而是通过普通人的视角重构历史 —— 相互搀扶的士兵、传递粮食的伤员、疲惫却坚定的神情,这些细节与抗战时期军民互助的集体记忆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感受到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另外,在《庆丰收》中的粮食与笑脸,提醒着我们,反法西斯的胜利不仅是战场的凯旋,更是战后建设家园的坚守、劳动创造幸福的朴素追求。
从记忆研究的视角来看,这类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并在后来的历史语境中不断被“再激活”,并逐渐升华为一种民族的“文化记忆”。图像作为记忆载体,使观者在不同历史时刻都能重新与过去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形成跨越世代的文化认同。
这些美术作品中的“艰难”和“笑容”,都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纽带——无论是革命的坚定,还是丰收和平的喜悦,都值得我们铭记,珍视。
文中作品
李春阳,文章《人民画报》(1950-1966) 美术作品的“革命性叙事”语言;载文期刊:《文艺评论》2023年第0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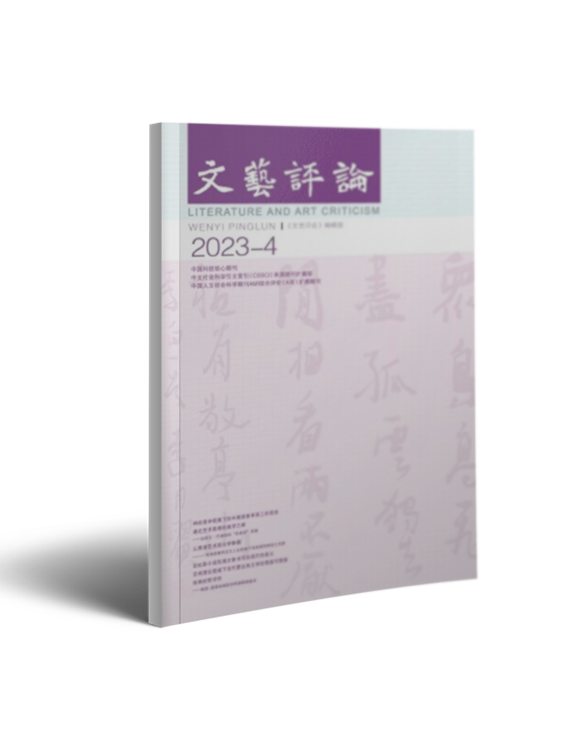
作者许钦松系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故宫研究院中国画法研究所研究员、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责任编辑:张馨宇
复审:穆宏志
终审:马雪芬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