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法学院法学和历史学教授罗恩·哈里斯所著的《远涉重洋:欧亚贸易与商业公司的崛起》一书,详细探究了中世纪后期,也就是14-15世纪起,欧亚大陆远程的海路贸易的组织方式。
在开端时期,这种贸易主要由若干短途贸易组成,由个体商人、小型行商主导,包括而不限于代理商、家族企业、小型合作关系和族群网络。尽管当时的不同地区和国家实行着不同的法律,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基于借贷关系展开的贸易都给出了比较明确的限制,但贸易仍旧得以冲破重重阻碍而广泛展开。
个体商人、小型行商组织的海路贸易,如同陆路贸易一样,有着漫长的历史。在中国的汉代和唐代,丝路和海上丝路显然保持着长期通畅,而围绕着这些贸易的融资、借贷、抵押以及商业合伙关系,已经发展到相对成熟的水平。可以认为,从中国南海、东南亚岛屿之间的海洋再到广袤的印度洋,以至阿拉伯海,海路贸易在古代跟现代具有共同特征,都是“资本、劳动、航海与贸易知识在甲板上交汇”。
书中探讨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对航海借贷等组织贸易模式提出的限制,强调这些模式其实冲破了宗教限制。而后转入对中世纪的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期间一种非常广泛的贸易促进制度,即康曼达制度的研讨。康曼达制度是投资人和行商之间的双方合同,约定双方的责任以及利益分配。这种制度最初出现在早期的伊斯兰阿拉伯世界,而后传入欧洲产生深刻影响,还曾在蒙元时期传入中国的南方港口城市,是对贸易风险和投资回报一种平衡性的设定。
毫无疑问,在现代公司制度以及更为体系化的股票市场出现以前,家族企业是前近代时期促进贸易的核心组织制度。书中对14-17世纪欧亚不同地区的家族企业运行情况进行了检视,指出家族企业在短中期运行相较于其他形式能够发挥出重要优势,但是“会遇到固有的外部限制”,比如少数商业贸易家族掌握大量财富,受到宗教组织以及世俗统治者的觊觎。此外,当时的家族企业也难以克服代际传承、资产分割等障碍。从本质上讲,如书作者所说的那样,家族企业模式的组织方式,无法长期维持大规模、财务稳定且能够从地理范围上覆盖整个欧洲、印度和中国的企业。
书中对欧亚一些地方中世纪后期和近代前期从事远洋贸易的商人进行研究发现,当时的商人在贸易扩张范围上,已经扩展到很高的规模,也有赖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对于财产权、贸易争端的成熟仲裁法律,但是传统商人制度相较于后来的现代公司制度,弊端仍然十分明显,比如很难有效平衡合伙人之间,以及公司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分配。
书中借由对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及大航海时代初期葡萄牙王室驱动的殖民冒险进行对照研究指出,尽管明代中国与同时期的葡萄牙王国,在国力上存在巨大差异,但本质上都属于统治者直属的国营贸易,贸易收益的分配往往主要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是推动产业、技术的增长、改变。更本质的问题在于,近代之前的国营贸易,虽然规模很大,以国家之力可以形成保护贸易的强大军事力量护航,但因为没有经历组织革命,所以长时期持续稳定的远程海洋贸易,对于国力非但不能滋养反而过度消耗。
在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出现的商业公司,相当程度上分别解决了前述家族企业、商人、行商以及国营贸易在长时期持续稳定开展远程海洋贸易方面的困难障碍。书中探讨了另一个重大历史难题,那就是从1600年前后商业公司首次出现在欧洲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期以殖民的形式侵入亚洲,商业公司也未能在三个世纪的时间内从欧洲前移到中东、印度和中国,未能使得这些地区出现本土发展的商业公司。
在奥斯曼帝国控制的中东,虽然帝国仍旧允许商人存在和活跃,帝国贸易也颇为活跃,比如与欧洲国家交易军火、奢侈品,交换金银,但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伊斯兰世界,古希腊城市传统已经丢弃,属地省份和城市本质上是满足帝国统治的征税单元和调集兵员的单元,而可能参与或卷入贸易的机构多为帝国控制下的行会。当地的城市、宗教学校和行会缺乏对自主且复杂的组织形式的需求。
相较而言,印度次大路上的德里苏丹国等国家的统治者,对于商业尤其是海洋贸易的需求更加依赖,但政治控制与社会组织体系之间的联系却是过度松散的,因而为家族企业、行商的继续活跃留出了空间。
对于中国宋代、元代、明代乃至清代而言,中央政府对于贸易的控制地位远超同时期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再加上中国社会中的宗族组织具有密切强大的组织性,使得家族企业、宗族成员组成的联合企业或者商帮,也能够满足维持贸易的需要。书作者指出,本质上,中国的儒家思想与王朝秩序,使得公司法系的概念也就是约束统治者、公司主体以及其他利益主体的法律不具备生存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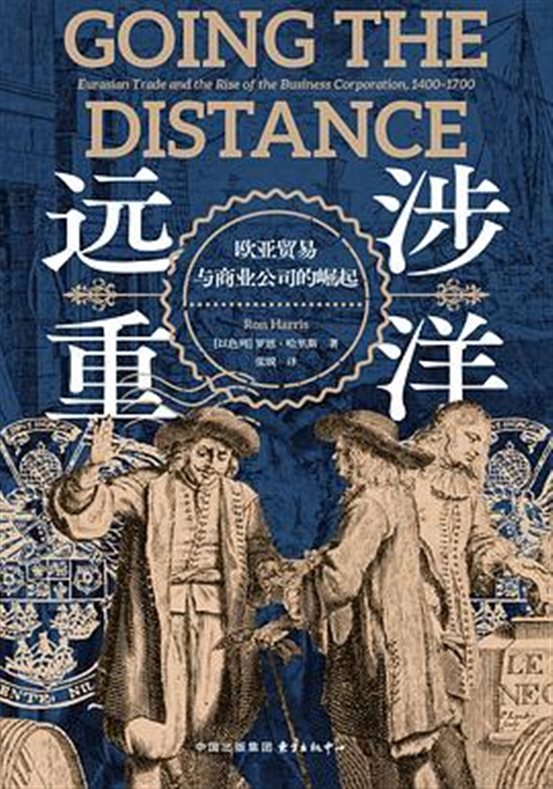
书名:《远涉重洋:欧亚贸易与商业公司的崛起》
作者:(以)罗恩·哈里斯
译者:张锐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4年11月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