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治理的宏大叙事中,街头作为国家权力与社会生活交织的微观场域,始终蕴含着丰富的权力互动与治理智慧。吕德文的《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以武汉市鲁磨路为社会学显微镜,通过沉浸式、饱和式的田野调查,深入解构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基层治理的核心命题,敏锐地揭示了街头秩序生成的深层逻辑:它既是国家权力的末梢展演,也是社会韧性的生动体现;既是制度性矛盾的集中呈现,更是中国式治理智慧的实践熔炉。通过展现城管与小贩之间既对抗又共生的复杂关系,为理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提供了极具深度的样本,呈现了一线治理的真实面貌,也从理论层面深刻反思了现有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鲁磨路,作为连接鲁巷和东湖风景区的重要通道,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复杂的社会生态。这里街道布局错综复杂,后街背巷众多,居民构成多元,高校、单位、居民小区与城中村相互交织。沿途几百家店铺,加之鲁巷地区作为繁华商业中心带来的巨大人流量,使得鲁磨路成为各种营生汇聚之地。从早年城郊地带的自然规划,到因“中国光谷”规划而进行的道路改造,再到光谷商圈形成后商业活动的迅猛发展,鲁磨路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空间不断被重塑,也引发了一系列治理问题。
书中描绘的鲁磨路上,残疾人的修鞋摊、老婆婆的杂货摊、烤馕摊、夜市等与城管执法车共处的场景,生动地展现了街头空间的拥挤与多元。这种空间的复杂性为城管与小贩的互动搭建了独特的“舞台”,也使得街头秩序的维护变得极为棘手。正如福柯在论述空间权力时所指出的,城市空间不仅是物理容器,更是权力运作的场域。鲁磨路的空间变迁过程,正是权力与精英、资本、民生需求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体现,城市空间的快速变迁与社会生态的多元性,是理解鲁磨路城管执法困境以及街头秩序形成的重要背景。
在一般认知中,城管与小贩往往处于对立状态,冲突事件时有发生。鲁磨路的情况也不例外,占道经营、无照经营、出店经营等现象比比皆是、屡禁不止,城管的执法行动常常引发双方的紧张对峙。整治周边环境的需求与摊贩的生计诉求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当城管严格执行法规,试图清理占道摊贩时,小贩们为了维持生计,往往会采取各种方式抵抗,这种对抗性的关系成为街头的常态景观。
社会学家科塞的认为,社会冲突源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鲁磨路城管与小贩的对抗,本质上是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分配矛盾的外在表现——城管代表的城市秩序维护需求与小贩代表的生存资源获取需求,在有限的街头空间中形成了直接碰撞。以鲁磨路“地摊王”李成柏一家为例,他们在鲁磨路占道摆摊长达10多年,期间与城管的冲突不断。李成柏面对城管执法,软硬兼施,甚至出现过下跪、撕整改书等过激行为,而城管在执法过程中也承受着巨大压力,这正是双方矛盾尖锐化的典型体现。
然而,深入观察会发现,城管与小贩之间并非只有简单的对抗。在日复一日的“猫鼠游戏”中,双方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与妥协。城管见着小贩本能驱赶,小贩见着城管摆出退缩模样,但很多时候这种互动仅仅停留在表面。在长期的博弈中,双方都明白彼此的底线,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例如,城管可能会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对小贩的经营行为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而小贩也会尽量避免过度挑战城管的权威,以免引发激烈冲突。
这种默契互动的关系,揭示了街头执法实践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将城管与小贩的关系归结为二元对立。这与戈夫曼“拟剧理论”中的“前台/后台”划分形成呼应。在街头这一“前台”场景中,双方展现出对抗性的角色表演;而在长期互动形成的“后台”默契中,又存在着基于现实利益的妥协空间。在鲁磨路,一些小贩熟知城管的执法规律,在城管巡逻的间隙进行经营活动,城管对此也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要不引发严重的秩序问题,双方就能维持这种微妙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互动模式深深植根于特定的街头文化生态。小贩们的经营行为背后体现着一种坚韧的生存文化——在有限资源条件下通过街头谋生获取生活来源;而城管执法则受到其职业群体文化以及社会舆论对城管角色认知的深刻影响,使得他们在执法时必须权衡自身形象与社会评价。更重要的是,鲁磨路周边居民的生活习惯与消费需求,与小贩经营活动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居民对夜市小吃摊的喜爱为小贩提供了稳定的市场基础,同时居民对环境卫生、噪音等问题的投诉又促使城管加强管理。这种基于地方文化和居民日常需求的持续互动,共同参与塑造了街头的文化生态与秩序格局。
城管作为街头官僚,肩负着维护公共秩序的责任,拥有行政权力;小贩则是社会弱势群体,为了生计在街头寻求生存空间。但这种身份的划分并非绝对,在实际互动中,双方的权力关系存在着动态变化,并在持续的博弈中重构着彼此的身份认同。城管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秩序警察”,而是在实践中逐渐转型为“空间协调者”,需要权衡多方利益;而摊贩也不再是单纯的“治理对象”,其通过集体行动和策略应对,实际上已升格为街头秩序的“共建者”。当城管严格执法时,权力向城管倾斜;而当小贩联合起来,或者借助媒体、舆论的力量时,又可能对城管的执法行动形成一定制约。
从制度层面看,城管执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占道经营、无照经营等行为进行管理。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执法资源有限、执法场景复杂,制度往往呈现出弹性执行的状态。鲁磨路的城管在面对大量摊贩时,无法做到对每一个违规行为都严格惩处,而是需要在维护秩序与保障民生之间寻求平衡。
这种弹性执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制度的严格性,但却适应了街头复杂的社会现实,成为维持街头秩序的一种现实选择。当正式制度无法完全覆盖复杂现实时,参与者会通过长期互动形成非正式规则,鲁磨路城管执法中的“弹性空间”,正是这种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补充与修正。例如,在鲁磨路夜市整治过程中,城管部门在执法时并非完全按照制度规定进行“一刀切”取缔,而是设置了15天过渡期,向摊贩普及城市管理法规,给予经营者充分的调整时间,这一做法在遵循制度原则的基础上,兼顾了实际情况,体现了弹性执行。
需要强调的是,街头秩序的生成不仅依赖于制度设计与执法实践,更是在复杂的社会互动与关系网络中逐渐形成的。在鲁磨路,存在着一个由城管、小贩、居民等多方主体构成的互动网络:小贩之间既竞争又互助,通过信息共享共同应对执法检查;居民通过投诉和反馈影响城管的执法重点与方式,同时又通过消费行为与小贩形成经济依存关系;城管则在执法过程中不得不综合考虑居民的生活需求和小贩的生计问题。这种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持续互动与协商,构成了街头秩序生成的深层社会基础,各方在这一关系网络中不断交换信息、调整预期、达成临时共识,最终实现街头秩序的动态平衡。
书中提出了“灰色秩序”的概念,深刻揭示了鲁磨路街头治理的特殊实践逻辑。在这一秩序下,城管与小贩之间长期形成的“猫鼠游戏”,实质上是城市空间实践中产生的大量灰色地带的治理回应,体现出半正式行政主导下的执行特征。这种秩序既体现为城管执法中的自由裁量空间,也表现为双方在日常互动中建立的默契与顺从模式。它在常规治理中有效化解了大量潜在冲突,抑制了暴力的显性发生,成为维持街头表面平衡的重要机制。然而,灰色秩序的存在也伴随着内在的脆弱性和潜在风险。由于弹性执行缺乏明确、统一的规范边界,治理行为中的不确定性不断累积,使得秩序的维系高度依赖双方的非正式共识。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例如政策突然收紧、社会舆论转向、考核节点、领导更替等,原有的默契便极易被打破。此时,灰色秩序中原本被压抑的矛盾失去缓冲机制,双方只能通过公开的暴力冲突来重新确立权力边界和行动规则。因此,城市暴力并非简单的个体行为失范,而是灰色治理机制失衡后的必然产物。譬如在夜市管理中因强力清退而引发激烈冲突,正是这种暴力再生产的典型体现。这也警示我们,任何试图骤然改变灰色秩序而不提供替代性制度通道的尝试,都可能触发更深层次的社会张力。
当下正值社会深度转型期,城管及其塑造的街头秩序面临巨大挑战,回望此书,其现实意义愈显深刻。《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启示我们,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其核心或许不在于消灭街头经济的“杂乱”,而在于发明能够容纳差异的新秩序形态。正如鲁磨路上永不落幕的“猫鼠游戏”所昭示的——那里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却有着社会最真实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这部城市民族志最终揭示:真正的秩序不在整洁的图纸上,而在生存与规则持续对话的辩证过程中。
同时,本书也提醒我们,在城市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寻求更加合理、有效的治理方式,以实现城市的和谐发展,引导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城市治理的本质与未来方向。正如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所强调的,有效的公共治理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鲁磨路的治理经验恰恰印证了这一观点——只有在秩序维护与民生保障之间找到动态平衡,才能构建真正可持续的城市街头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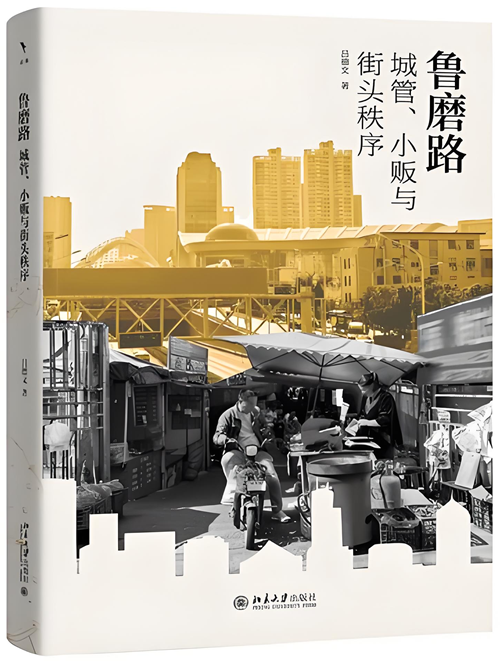
《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
作者:吕德文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7月版
ISBN 978-7-301-36334-8
定价:66.00元
(供稿:张丽霞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