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的成长时期,欧洲的政治秩序可以简约概括为梅特涅策划和建立反民主主义的君主同盟。这一秩序不仅强烈反对拿破仑式的共和,反对社会契约理论,而且连开明专制主义也不允许。
欧洲强国中,英国抽身于外,俄国沙皇、哈布斯堡皇帝、普鲁士国王就是大陆秩序的捍卫者。尽管包括这几个大国内部,也浸染着当初拿破仑释放出的宪政精神和民族主义。
有人追求民主和自由,就有人反过来去捍卫秩序,每个历史时期都不存在一边倒式的群体选择和行动进程。新引进出版的《俾斯麦:欧洲风暴》一书谈到,俾斯麦成长于欧洲的革命动荡时期,他依照普鲁士,亦或者被并吞之前的萨克森的贵族思维来看待这一切。他需要去捍卫家族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他接纳了贵族感情、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还有父辈、家族、阶层赋予的社会联系和纠葛。
当然,19世纪前半叶的德国农村中,所谓贵族,无非是大大小小的容克地主。俾斯麦就读的学校,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以及之前曾一度接纳了法国式的教育方式,也就是启发式教育,但很快这被普鲁士的爱国运动取代了,更加强硬而机械式的教育方式贯穿了对这个将在日后统一德国的男人的青少年教育。学校不会让孩子吃饱,强硬推行按部就班的作息,灌输爱国主义。他自己将之称为“人造的斯巴达主义”。
俾斯麦的母亲,对待他以及其他子女都以严苛著称。而他的父亲则要温和许多。但有意思的是,俾斯麦的母亲威廉明妮其实非常倾慕人文主义和科学,而老俾斯麦则抱持着传统的容克地主的世界观。母亲对他的教育是失败的,他义无反顾地拥抱了德意志的爱国传统。
但与同时代的很多人相较,俾斯麦又带有更多的特殊性。他接受宗教课程,但又对宗教抱以怀疑态度。他在年轻阶段,自己的同学热情高涨地投身支持普鲁士民族主义,追求新闻自由,希望效仿之前的法国建立宪政民主。俾斯麦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成长,却与包括各种自由化的学生社团抱持距离。
这并不是说,年轻的俾斯麦在心智上已经成熟到后来的地步。如《俾斯麦:欧洲风暴》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俾斯麦当时其实要算是个非常浪荡的青年,胡吃海喝,他的开销甚至超出了一个容克地主家庭所能承受的范围。他染上了赌瘾,对待学习更是应付了事。总之,他经过“放荡、大胆、债务缠身且忙乱的大学生活”,最终选中了自己的职业道路,那就是成为普鲁士的外交官,期待成为下一个塔列朗或梅特涅。
这种期待在当时,无论是俾斯麦自己还是密友,都当成最离谱的玩笑话。
俾斯麦渡过大学生活的方式,某种意义上使得他错失了凭借自身才智成长为类似于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这样的严肃学者的可能,他也不被黑格尔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政治理论所浸染。他对政治的理解,一早就依照自己的爱国主义传统,以及阶级出身而确定。
俾斯麦曾经有过一段重要恋情,但恋人是英国人,而且还谎称自己是贵族。这让俾斯麦深感愤怒。我们显然不能因此就断定俾斯麦在成长为德国首相后,与同时期的德国诸多政客所不同,摆脱了英国滤镜,而是冷静而讥诮地愚弄英国、麻痹英国,就是多年前英国恋人的欺骗。但是人的思想倾向与感情倾向似乎有时不可能截然断裂开来。
1838年,23岁的俾斯麦放弃公务员的工作,回归成为一个庄园主。这其实是磨平俾斯麦性格中的狂躁的重要选择,他在普鲁士自由主义浪潮最汹涌的情况下,回归容克地主的生活——而当他回归时,不但资产阶级甚至初生的无产阶级各自发展出革命派别,而且新旧贵族地主也建立起政治上的代言群体,也就是反对革命的派别。
俾斯麦在庄园醒觉了对于地主制度以及其他一切封建制度的热爱,并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来赋予其合理性。在德意志四分五裂的政治环境下,容克地主本就是新工业的参与者,这似乎进一步增添了他捍卫旧制度的信心。书中谈到,在庄园,他增强了自我意志,更加迫切地希望以自己策划和行动的方式去捍卫自己想要捍卫的制度。
虽然这期间,俾斯麦也在不断阅读,但思想结构既已确定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接受诸如单方面融入西方、对抗俄国的政治思想。他跟随自己的父亲参加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依据传统举行的继位典礼,而对于南德意志地区勃兴的自由主义,他深感厌恶。
1845年,老俾斯麦去世。俾斯麦重新投身政治。他将在十多年后才树立德国的保守主义,需要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相妥协的思想。在19世纪40年代的他,对于旧制度岌岌可危的现状忧心忡忡。1847年,俾斯麦完婚,并作为新当选的第一届联合省议会的代表,以惊人的粗鲁反驳了自由主义反对派对于普鲁士宪法的期望。他展现出惊人的忠君立场,将自由主义对于民主、宪政的追求统统指斥为离经叛道,对于批评普鲁士政府政策的做法都进行了道德上的质疑。
这一阶段,俾斯麦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政坛上的斗士。他不仅以一己之力激烈反驳和质疑自由主义反对派,而且寻求反自由主义的集体活动。马克思,以及同时代不同革命倾向的政治和思想精英办报鼓吹革命,俾斯麦也和友人一起办报。
德意志的自由主义浪潮,以及革命浪潮,主要活跃在大城市,以及资本主义工业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所以这意味着容克地主势力集中的农业区和城市,俾斯麦寻求的反对革命集体组织,也是比较容易构建的。虽然此时他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所以在1848年革命中,普鲁士的革命浪潮虽然声势浩大,却狼狈走向失败,当然从历史的后视视角而言,这也避免了普鲁士在当时招致沙皇俄国的粗鲁干预。
不仅如此,虽然一些规模较小的德意志邦国,事实上由自由主义反对派发起设立了很多进步型的政纲,比如废除或放松审查制度,吸纳自由派到政府部门或将之派遣到邦联议会,但普鲁士保守主义站稳脚跟,则对上述进步进程予以了最严厉的叫停。
1848年春,英国政府残酷镇压了要求普选权的宪章派势力。普鲁士军队在波兹南镇压了波兰人的起义。巴黎六月起义,也招致了血腥镇压。在德意志范围内,自由主义反对派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充满了软弱性,但是从之后几十年的斗争历程来看,自由主义反对派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于政治参与空间的争取,他们放弃的只是与无产阶级的合作,如果保守主义者愿意给他们参与机会,他们就愿意与俾斯麦这样的人合作建立政府。
事实上,日后精明操纵欧陆政治进程的俾斯麦,此时也基本上褪去了作为政治新人的青涩。参加竞选,他心知保守派在群众中不受欢迎,所以大谈特谈赞同宪法,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又委婉地表示反对废除贵族制度,反对削减普鲁士的军队。这种含糊其辞的表态,一方面继续取悦君主以及容克大贵族,另一方面也保住了一部分群众票额。
在平息1848年革命的余波后,俾斯麦加速了政治经验积累,日后的政治倾向更加明显,他排斥法国,认为哪怕是拿破仑的侄子操弄的拙劣宪政,也有导致法国乃至全欧洲复活法国革命的危险。他醉心于挑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系,在1849年之后的一些年里,这种挑唆最初停留于他个人的想象,而当他获得政治权位后,尽管并未明确获得这方面的授权,也坚定不移这样去做了——奥地利,更准确来说哈布斯堡帝国,在1850年就已经在俾斯麦心里判处了政治死刑。奥地利并不愿意作为德意志地区的盟主完成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一统,也反对普鲁士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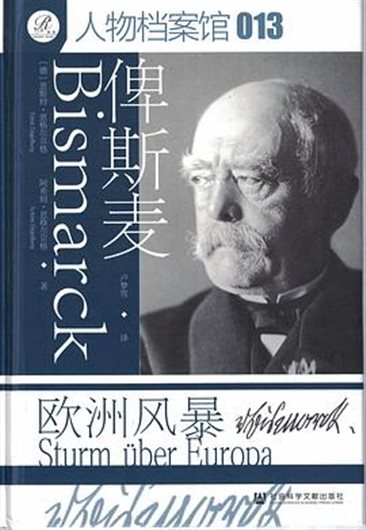
书名:《俾斯麦:欧洲风暴》
作者:(德)恩斯特·恩格尔贝格、阿希姆·恩格尔贝格
译者:卢梦雪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6月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