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东汉后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获得大规模开发。这也是唐代作为强盛与汉代并列的朝代,江南成为天下著名的富庶之地。唐中后期,北方面临割据以及战乱、入侵,江南各地的经济地位更加重要,农业深耕。至于宋代,一年两熟在江南全面实现。
元明时期,江南的开发显然经历了所谓的先抑后扬。南宋都城地处江南,灭掉赵宋的元政府当然要继续依赖江南税收,但也尽可能抑制发展。而明朝建立之初,淮西豪右与浙东文人集团的博弈,使得江南地区无论在士子选拔还是经济开发上都受到一定抑制。明政府将都城从应天迁往北平,降低了江南地区的政治地位。
但有趣的是,这也为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丝织、棉纺织等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发展铺平了道路。新的棉花经济、蚕桑经济依然保持着地主与小农、佃农并存的农村结构,但生产单位不可避免地卷入市场化。而浙西不适合粮食和棉花生长的地区,则广泛种植茶、桑、竹、木。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江南地区开始迎来大规模的市镇化。
唐宋时期,以及这之前在江南地区出现的城市、军镇,一般是军事意义上的,并满足政治治理功能。但晚明在江南出现的诸多市镇,则是纯粹商业化催生的结果,也就是过去的自然村落因为商业化机遇而成长为更为显著的经济中心。
按照学界统计,仅太湖以东苏州府和松江府,1551到1722年的100多年里,市镇数量就从161个增加到261个。到了清末,江南地区的市镇数量超过千个。
基于商业化形成的市镇,就是介于县治以上城市和农村定期市之间的聚落,出现了雏形化的自治机构,还有手工业体系,另外还分布了各类庙宇。
很显然,相较于当时中国其他地区,江南地区因为商业化市镇的快速膨胀发展,因而变得更加富庶。而这也意味着农业前所未有深入地卷入商业体系,市镇人口比重在总人口中提升,而士绅阶层对于市镇甚至更广大意义上的城市、农村的影响力也会急剧增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历史学者、东华大学副教授、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杨茜所著的《市镇内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一书。这本书深入分析了晚明江南商业市镇崛起过程中,同步成长的士绅家族。
这些家族一方面积极兼并土地,辛勤经营,并涉足金融、贸易多项产业,在财力上成为不亚于北方地区从事边贸甚至垄断物资经营的豪商的力量,另一方面则积极培养家族中的佼佼者参政。仅南浔镇异地就先后走出了朱国祯、温体仁、沈演等五位中央级高官。这些家族还成为江南城市和市镇园林文化的塑造者。可以认为,市镇家族在当时的江南形成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支配力量。
《市镇内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书中讨论了江南商业市镇的快速壮大如何与特定家族的经营活动相辅相成,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出现了大量的“主姓市”,也就是冠以“唐市”、“李市”、“何家市”等大族姓氏的市镇。尤其是嘉靖到万历年间,常熟地区新涌现的17个新兴“市”,无一例外都有家族创市的记载。这些大族创市,确实也有过突出的贡献,包括积极带领开浚河流、晚辈灌溉,还有就是主导鱼盐开发。士绅家族还成为兴筑桥梁、建造房屋的积极出资者,加快市镇把握商业化潮流机遇而茁壮成长。为了抵御倭寇入侵,一些商业化市镇也同时主动兼具了军事防御功能。
这本书借助文献记载,讨论了市镇扩容过程中,士绅家族如何通过生产经营、贸易和金融投资来壮大家资,以及在乡里投资操持公益事业以积累声誉。但书作者也同时强调,当时的江南地区赋役繁重,所以士绅家族要维持和发展家业,还必须不断致力于培养家族精英参与科举竞争,否则将不足以形成自我保护。如果一个已经发家致富,远近拥有支配力的士绅家族,连续几代未能涌现出科举精英,将很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被权势以及竞争者(其他士绅家族)吞噬掉财富。
反之,如果一个家族在科举竞争中连续涌现出佼佼者,那么甚至能够反过来参与甚至主导县政管理,也拥有觊觎和并吞其他家族财富的主动权。毫无疑问,明末东林党成员,明清鼎革之际主持坚决反清斗争的知识分子,有相当数量出自于这些市镇的士绅大族——他们一方面反对明政府将稳定天下的财政责任不断增加转嫁给本地区,但另一方面在明政府倾覆时,又组织反抗斗争。
清代以后,江南地区的市镇士绅家族依旧广泛存在,虽然明清鼎革之际,很多家族遭遇了灭顶之灾,但和平恢复后,商品经济得到复苏就重新赋予了这些家族的成长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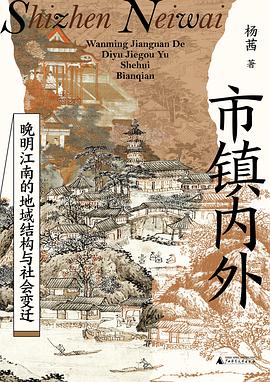
书名:《市镇内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
作者:杨茜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8月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