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的欧洲城市,规模通常不大。当时最大的城市伦敦、巴黎人口不过数十万,而10万级人口城市柏林、汉堡、慕尼黑、米兰、罗马、那不勒斯、维也纳,在日后都会成为国际级都会,不过当时与过去的商业城镇、行政城镇并没有太本质的区别。至于华沙、布达佩斯等城市,人口规模就更小了。
如果踏足当时的欧洲城市,很可能被城市面貌所欺骗。各地的城市或布满基督教的教堂,或是其他宗教的建筑,这些在当时的人们生活中有着持久的影响力。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是非常缓慢的。
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福特汉姆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斯玛丽·韦克曼在其所著的《欧洲城市现代史:从1815年至今》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欧洲城市的快速发展起步于18世纪晚期,在19世纪初进一步加速。各种城镇不仅有了显著发展,农业生产的扩张和新型工业的到来,使得小城镇甚至过去的乡村聚集点开始有机会成长为拥有遥远交易网络的活跃贸易中心。
对于当时的城市而言,工业化进程的势头如此迅猛,以至于不得不拆掉过去的城墙,重建城墙,然后依次累进。城市里涌进大量的异乡人,包括失地农民,季节性劳工,熟练的工匠,教士、官员、士兵、海员,流动小贩,政治难民。“这是一个充满机会和扩展视野的世界——富人和穷人、受人尊敬的市民和卑微的新来者在街道上摩肩接踵。”
城市的财富增长,冲击着城市原有的自治传统。过去的贵族、行业会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身份特权,但新增利益对于人们构成如此的诱惑,以至于过去以来的很多规训开始变得没有意义。
书中指出,1800年后,欧洲的人口增长到2亿,有相当比例的人口聚居在高密度的定居区,形成人口稠密的村落、城镇和城市景观。英国、荷兰、比利时以及意大利有最悠久的城市历史与最密集的城市网络,而在欧洲南部如意大利,则比欧洲北部的城市体系更繁盛。欧洲东部的城市化程度较低,也更多情况下被视为野蛮的聚落。但无论如何,城市化洪流都将对这些地区构成不断冲刷,较大程度上改变其面貌。
如书中所谈到的那样,欧洲各地的海岸城市,以及泰晤士河、莱茵河、鲁尔河、易北河、塞纳河、罗讷河、加龙河、维斯瓦河、多瑙河的许多沿江港口城市,从谷物贸易的兴起,培育出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发展出专门的物流体系和加工体系,催化出海运设备、军事装备、酿酒、锻造、皮革、纺织品生产等产业。港口地区的人们变得精于算计,也因为汇集了大量的异乡人而重塑本地与外地的关系。
19世纪初,俄罗斯帝国还在急剧扩张之中,这对于波罗的海世界、黑海世界的很多城市造成了很大影响。波罗的海的城市,交织着俄国人和德意志人的习俗,还有本地文化的激烈交锋。俄国占领这些城市,包括里加、塔林等地,允许其保留原有的贸易传统以及德意志文化,这一举措也使得波罗的海地区的城市塑造出单独的身份认同,向往欧洲。
而在俄罗斯增强南部经营,不断侵蚀奥斯曼帝国属地的过程中,敖德萨等城市兴盛起来,其战略地位甚至要超过帝国的其他很多城市。因为其扮演着输出粮食,为欧洲各地城市提供喂养的功能的角色。同样,敖德萨也因而变成欧洲最具国际化的城市,如《欧洲城市现代史:从1815年至今》书中所说,这里的多元化人口和城市文化,植根于奥斯曼的民族拼图中,由各种人组成,尽可能实现共存。但这个城市曾经的奥斯曼属地、19世纪以后的俄国城市属性,也使得其对于欧洲各地的旅行家而言倍感矛盾:既是欧洲的,又有浓烈的非欧洲性。
在罗马尼亚,以及中东欧的其他很多城市,随着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势力的此消彼长,贸易未曾断绝,但城市的控制权不断发生转换,而城市面貌也会经常性地重组。在长时段,这些城市都延续着种族共存、宗教宽容,但剧烈的战争以及瘟疫灾害期间,种族和宗教矛盾却容易被激发出来,成为湮灭城市活力的引子。
而在英国以及西欧的其他一些国家,工业革命重新定义的制造业在改变城市的发展路径。贸易突破了对于农产品交易的依赖,过去的农村、村镇手工业渐趋消亡,以全欧甚至全球市场为导向的制造业布局到城市。这刺激了建筑建设,而且金融、产业投资因而变得踊跃。如书作者所谈到的,英国不少地方的城镇成长为充斥“工业巨兽”的地带,集聚大量的就业人口,而这使得城市空间变得进一步狭窄。当然,欧洲其他很多地方的城市或因为传统行会力量强大,或因为教会、世俗政府的压制,而使得相关的投资受到压抑,连带着使得这些城市失去了工业化的机遇,在未来的几十年甚至200多年里沦为无关紧要的地带。
待到19世纪中叶,欧洲的工业城市、城镇开始逐渐朝着现今的形态转型,配置更为良好的生活便利设施,不仅生产产品,而且为富裕起来的投资、管理阶层以及中产阶级提供消费条件。这些城市更多地采用煤气灯照明,为消除瘟疫而开始配建自来水管道。此外,消防、警察、图书馆等公共服务也开始被组织。虽然如此,工业时代的城市也仅仅能相对洁净,而无法彻底地清除各种污染,对于社会层面的压迫和掠夺更是置若罔闻。
类似的景象也出现在快速工业化的德意志。相较于英国和法国,德意志从农村、农业状态转向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时代冲击更为明显,人们也更加不适应污染的空气和土地。城市化的起步,虽然是以摧毁人的健康为代价的,但是聚拢在城市的贫民人口,相较于分散居住在农村的人们,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城市化和工业化初期,无论在德国还是法国、英国,人口迅猛增长。城市如同吞金巨兽,不断消耗着日益增长的粮食和各种生活物资。再加上有意营造的新型消费环境,这无疑为进一步的贸易创造出良好的条件。
《欧洲城市现代史:从1815年至今》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欧洲城市史,书作者不仅考察了传统的西欧城市,也深入探究了很少被历史学家和城市研究者纳入考量的波罗的海、东欧、巴尔干、西南欧的非首都城市,强调各地城市都有值得书写的故事,而现代性开启后再各地激起的反应和协奏也各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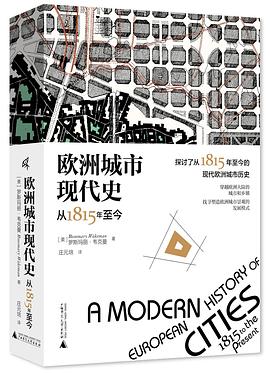
书名:《欧洲城市现代史:从1815年至今》
作者:(美)罗斯玛丽·韦克曼
译者:庄元培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8月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