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美国律师戴维·罗森汉恩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报道。罗森汉恩认为,精神病学的研究与临床,不足以区分理智和疯狂。他在文中分享了此前一年进行的非凡研究的惊人成果。
罗森汉恩偷偷将8个心智正常的人送入美国不同州的12家精神病院(其中有人在多家精神病院办理了住院)。这些假病人伪造了自己的身份,改变了年龄和职业。他们提前给精神病院打电话预约,抵达后就抱怨自己听到三个词的声音“空虚”、“空洞”和“砰”。
这些假病人成功入院后,会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没有再听到声音了,一切表现如常。这些情况被护士如实记录,报告给医生。虽然如此,这些假病人除一个人被诊断为躁郁症外,全部都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住院时间分别为7天到52天不等。
无论是护士还是医生,没有人提到这些人明显心智正常。
这篇调查报道在美国,甚至当时的世界其他很多地区都引发了对精神病学以及从业行业的抨击。
罗森汉恩故技重施,宣称将派遣一批假病人去美国一家大型教学医院,表示对方将无力甄别发现。这家医院在之后的一年里评估了193名新患者,认为41人可能是假病人。但罗森汉恩欣喜若狂地揭晓表示,他没有派任何人去医院。所以,他下结论说,精神病学无法区分理智与疯狂,该行业的日常行为无异于将无辜之人定罪并判刑入狱。
医学同行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精神病学的幻灭感。而保险公司大幅削减了保单中的精神健康保险。
反精神病学运动在20世纪后期的欧美曾多次兴起。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就曾撰写《疯人院》一书,甚至认为精神疾病其实不过是社会无法理解特立独行之人的动机,构建起所谓的隔离世界,事实上是戕害正常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杰弗里·A.利伯曼,与美国神经学家、科普作家奥吉·奥加斯在合著的《从弗洛伊德到百忧解:精神病学的历史》一书中谈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精神病学四面楚歌。
虽然反精神病学运动存在许多不同派别,有的认为精神疾病确实存在,但否定当时的治疗思想和药物,也有人否认精神疾病的存在,或将精神病患者认为是普通人,或认为是天才,反对干预,但对放纵精神病患者造成的社会影响往往避而不谈。
这一运动如同历史更为悠久的反疫苗运动,在公共卫生史上都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这一运动正确地揭示了药品公司、精神病学研究和临床机构利益驱动,所导致的过度标签化、过度治疗现象,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患者的病症危害性叙述,并扩大了患者基数,造成一种颇为悖谬的现象:美国等国家,在没有出现专业的精神疾病研究、防治机构以前,城乡居民基于生活印象对于患病者存量本就有感性判断,这类病人确实有——但在出现专业救治机构后,这类患病者的数量似乎过度增长,甚至将一些行业的从业者,因为其共同具有的日夜颠倒、过长加班等特点,而一致被诊断为精神疾病。这让大众对此充满了怀疑。
人们质疑的是,明明并不很严重的精神疾病,或者说明明“看上去”没有得病的人,却被诊断为精神疾病,这究竟是科学诊断,还是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呢?
这种质疑肯定有其道理,能够找到甚至大量找到过度治疗、错误诊断的例子,但是完全否定精神病学,以及其指导展开的诊治,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质疑过度治疗,甚至否认精神疾病而耽误治疗的例子,只会更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反精神病学运动中获得“经验”的一些专家,活跃在社交媒体上,一方面大谈特谈精神病专业治疗依赖药物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则设法推销基于心理暗示的各种所谓的新式疗法。
《从弗洛伊德到百忧解:精神病学的历史》这本书讲述了精神病学诞生、发展的全过程。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非洲、欧洲,以及近代阶段,精神病学以不同名义存在,人们曾普遍认为这与中邪相似,或者说患者本身存在道德缺陷,很多医治方法非常残忍。中国北宋曾有多任帝王在中年出现非常明显的精神疾病表现,即便以君王之尊,其能获得的治疗和保障也是非常不人道的。
精神病学作为学科,最初壮大发展的基础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得出过许多睿智而具有先见之明的观点,比如互补和竞争的认知系统理论,就构成了现代神经科学的基础,已经在先进的视觉、记忆、运动控制、决策和语言神经模型中得到了体现。而弗洛伊德的心理发展阶段论则构成了现代发展心理学和发展神经生物学的基石。但是,弗洛伊德过度自信和独断,使得其很少愿意去反思和改进那些被明确证明为错误的判断。
如前述,20世纪70年代,精神病学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陷入巨大危机。也同样在这一阶段,精神病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开始经历精确的数学化进程,也就是依托于数据而非主观臆断或传统分析。再后来就是磁共振成像(MRI)为代表的可以揭示精神障碍生理存在的脑部成像技术,生物精神病学、神经影像学和神经科学等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不仅为精神疾病获得确切诊断提供了条件,而且还为人们加深对于大脑功能及其运行方式的了解创造了条件。
在科学家和医生还在围绕精神分析是否继续适用于精神病学临床的同时,20世纪的美国和欧洲企业也意识到精神疾病本身创造出广大的空白市场——利用一些成瘾药物来抑制精神疾病的突出症状,后来专门设计出一些成瘾性相对较弱,可以平抑精神疾病狂躁表现的药物。凑够镇静剂、安定药再到氯丙嗪、丙咪嗪,精神药物让精神病学三大疾病中的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从过去完全无法治疗转变为很大程度上可控。
当然,这类药物耐药性的出现,以及美国等国家社会人群中相当部分成员过度依赖精神药物,虽然得以抑制和治疗部分疾病表现,却又额外造成了药物成瘾问题的泛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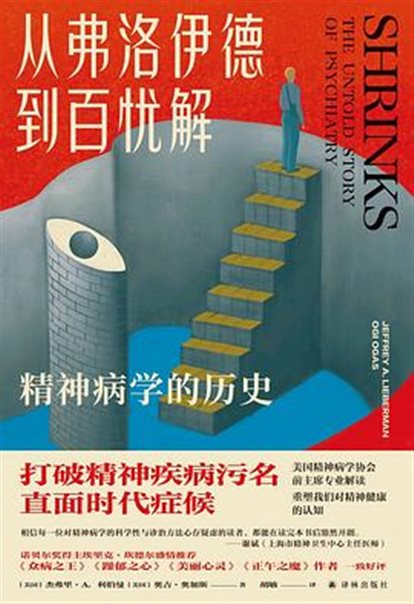
书名:《从弗洛伊德到百忧解:精神病学的历史》
作者:(美)杰弗里·A.利伯曼、奥吉·奥加斯
译者:胡敏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8月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