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家伊利亚德曾在《神圣与世俗——宗教的本质》中试图从神圣和世俗这对充满张力的范畴入手去探求宗教的本质。他认为“神圣”作为宗教的本质,往往通过“显圣物”而到场,因而“显圣物”既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宗教的人总是不断发现和建立各种显圣物,以此为中心展开自己有序的世界和宇宙,使自己能够生活在神圣之中。在庞大驳杂的中国神灵信仰谱系中,厕神就是是一个充满这种复杂二元对立的代表,神位不高却神力周遍,既诠释了污秽与洁净文化观念,也融合着普遍性俗化与神圣性显现。
刘勤在其出版的《神圣与世俗之间——中国厕神信仰源流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8月)一书中就沿着伊利亚德的进路阐释了此观点。他从“神圣与世俗”这对框架入手,系统探究了中国厕神的形态、缘起、定格、演变、流布、遗存等问题,清晰描摹出中国厕神的变迁轨迹与发展路向,为我们“撩开了一个隐秘又迷人的新世界”。
《庄子·知北游》中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在庄子这里,“粪”被赋予了形而上的意涵。万物皆有灵,粪自然也不例外,有粪自然就有粪神。刘勤辨析了厕神与粪神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厕之空间形成之前,厕神崇拜更多是粪神崇拜。那么粪这种“污秽之物”的“神圣之源”是什么?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厕的主要目的是“积粪”,这构成了粪神信仰的底层逻辑。一方面,粪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在古代农业社会,人们发现粪便、动植物腐蚀物浸润滋养下的土壤更具生产力。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旧俗,正月望夜迎厕神,谓之紫姑。”紫姑最初是厕神。《荆楚岁时记》又云:“(正月初一)又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今北人正旦夜立于粪扫边,令人执杖打粪堆,以答假痛。又以细绳系偶人投粪扫中,云令如愿,意者亦为如愿故事耳。”有学者从原生态神话的角度,由南朝以来的“锤粪”习俗等推测紫姑信仰源自古老的粪土崇拜,并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粪肥有关的粪神、厕神,自然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另一方面,粪与孕生紧密相连。女子的生产过程,从可视化的角度,与“排泄”过程相同,而产妇顺产的同时也经常排便,“粪便”便与生命的关系建立了可能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原始的粪尿崇拜。
此外,粪还是财富的象征。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的国策下,大力奖励农耕,而在农业中,粪又是最重要的基肥,施粪是粮食增产的重要条件。东汉班固在《汉书·沟洫志》中说:“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也将人畜粪尿列为“六肥”之首。甚至,自宋代始粪便成为可贩卖的商品。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记载:“杭城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粪便成为“倾脚头”的生财之道。
刘勤认为对“粪”的界定很重要。他辅之以文字朴学辨析甲骨文中的“粪”和“弃”字本义、“子”的本义等。他指出,“粪”与屎相关应是关键,屎是所有污秽之物中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并作出推测:“很有可能最初‘粪’和‘弃’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同一字。”“粪”实则隐射着以生殖女神崇拜为基础的大母神信仰。在中国古代的意境中,最早的“粪”字,自然不只是纯物质的“粪便”,既表示一切死亡,也表示着生殖与创世, 还表示着给予地母的礼物等观念,这构成了中国厕神的信仰来源。
美国作家朱莉·霍兰曾在《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中指出:“文明并非从文字开始,而是从第一个厕所建立开始。”农业定居、粪肥积累、畜牧业(尤其是养猪业)的发展,都呼唤着固定的厕之空间的形成。刘勤探讨了南方干栏式建筑、北方穴居式建筑、早期四合院式建筑等的人厕和猪圈空间,进而分析了厕之空间的功能、特征与鬼神信仰。在厕之空间形成后,首先作为便溺之处与积粪之所,粪神信仰与厕之空间信仰结合,并由厕所空间信仰中衍生出诸多厕所禁忌,如方位禁忌、行为禁忌等。设立禁忌是为了规避危险,为了规避危险,就要驱离污秽,而驱离污秽,就要清洁或者洁净,由此展现了厕之空间如何被赋予神圣性的复杂生成逻辑。
同时由于人厕与猪圈在早期的合一形制,不仅粪神与厕之空间合流,而且猪神信仰也与厕之空间合流,厕神的神格最终得以逐步确立。“粪”“厕”,以及一切肮脏、不洁、蠢笨等否定形象,都与猪是同位关系,猪被视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污秽。而且猪生活的空间,同时又是厕所空间,因此厕神还往往表现为恐怖猪怪,如《太平广记》描述“有厕神形见外厩,形如大猪,遍体皆有眼”,而这源自人类早期对猪(野猪、家猪)的崇拜和集体记忆,且常常经验为大母神的负面恐怖神格。
厕所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联结着阴阳与生死。刘勤指出,从空间论的角度,职司厕所、屎尿、粪肥、排泄、污秽、垃圾、牲畜(尤其是猪)等有关“污秽”(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事项构成了其基本神格,这是厕神之所以为厕神的基点。在此基础上,这些神格又扩大化到涉及田产、产桑、生育、疾病和死亡等。由此,不难发现厕所具有显著的“双面性”,它既是充满负面意涵的“至秽之所”,需要疏离和遮蔽,所以厕所常居于屋后侧,同时它又通过特定的仪式与法则,在污秽中“异化”为洁净,进而生产出神圣性,成为生命的赐予者,被视作治愈和再生的空间。正如日本学者范岛吉晴所说,厕所是具有不净、恐怖等否定性形象,是人类控制不住的空间,但另一方面,厕所通过这种否定性形象,成为创造新的东西的场所,“它是兼有破坏和产生的两义性空间,是我们内部的异界”。厕所,既是污秽的,又是神圣的。
透过神圣与世俗的矛盾统一性这一视角,该书不仅在社会信仰层面展现了污秽的厕所空间如何生产出神圣性以规范、制约与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从个体行为层面诠释了百姓如何赋予污秽空间的洁净行为以神圣的内涵,从而规避污秽空间可能产生的危险。正是从厕神这一细小而隐秘的基点,我们得以管窥微观日常生活与信仰文化体系充满意味与别具趣味的一种互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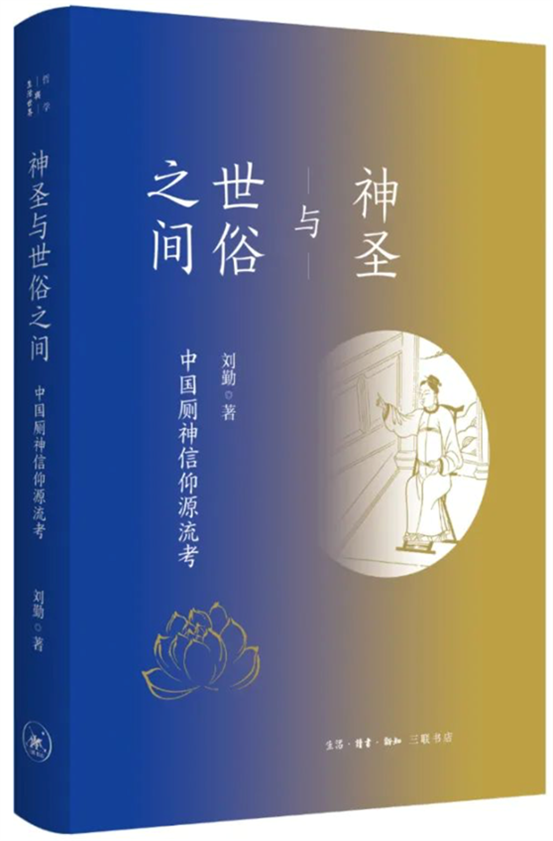
刘勤,《神圣与世俗之间:中国厕神信源流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8月第一版,98.00元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