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翟学伟所著的《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一书,近日推出精装版。这本书最早出版于2004年,经多次再版,仍广受欢迎,显现了书作者对于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人情、面子、亲缘关系等现象的深刻洞察能力,以及以此进行的学术梳理。
中国社会中的关系,可以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人际关系”这一舶来名词,指的是个体之间的各种关系,或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或行为倾向。但人际关系、互动、交流、社会交换、交互性等概念显然都不足以说明中国式的关系。
相对而言,为人处世、交际、应酬、做人等意思更接近于中国式关系的概念本身。当然,中国式关系涵盖的范围很广,可以在哲学、伦理学、民俗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纳入研究。
这本书分析认为,中国式关系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考察,即人缘、人情、人伦。人缘或者说缘分,指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中国古代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所以,人缘包含了血缘、地缘、姻缘、业缘、机缘、良缘、孽缘等多重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人缘也有善于待人接物之意,如“人缘好”的说法。人情一方面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纳入伦理规范因素——这也由此与人伦相关。
书中指出,考察中国式关系,需要理解自古以来,中国的天命观、家族主义、以儒家为中心的伦理思想。中国的天命观与宗教中的人神关系不同,事实上周代殷商以后,天就逐渐从较为纯粹的神格、神意转化为了命运、机遇、规则之意。尤其是在本土化的道教发展,以及外来的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通常相信天是强大的势力,可以操纵人的行为,赏罚人的善恶,但天命并不意味着人要一味服从和等待。家族关系则是适应中国农业社会的最重要伦理关系、经济关系,由此发展出血亲传承、倡导大家庭、敬奉祖先等观念。儒家为中心的伦思想之所以能够占得主体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些思想要求一个人立身守信、守仁为基本,逐渐推导至家国理想,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与逻辑上的一致性。
所以,探讨中国式关系,必须意识到,建基于伦理,发展依托于道德,并不同于西方式的人际交往的等值性特点。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情交换讲究的是安土重迁和血缘关系依托的交往长期性、连续性,所以算账、清账是不通人情的表现。
中国人际关系重情,而这个情依托于礼,内核为仁,用儒家的说法归结为“忠恕”。儒家伦理将人伦融入人情,使得血缘亲情具有伦常性,这在很长时间内使得家庭、家族、地区社会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当然,这对于其中部分个体的约束和压抑也是相当明显的。
人缘的核心是“缘”,如前述,这加入了宿命论的观点,也就是人的一切遭遇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前定好的外在必然性——可以将这种观念理解为对劳动人民的麻醉剂,因为受此影响,人们便会对很多现状不再执着。也就是说,人缘、人情、人伦构成了密切衔接的中国本土化关系模式。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书中由此引入社会学理论,借助个案分析,剖析了中国人关系网络中的结构平衡模式。按照书作者的观察,平衡性是中国人际网络交往中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原则,在多人关系中通常会自然出现制衡性,而这种制衡性往往会在平等的交往者之间稳定实现——时间较长的情况下,这会构成一种心理压力,导致处于平衡结构中的各方尽可能做与他人同样的事情,来压抑自己原本的意愿。书作者举例来说,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很多患者因为担心自己不送红包会招致医生的差别待遇,所以哪怕医生反对,也要坚决送红包——这就是平衡性的要求。
近年来更常见的例子是,基于微信、QQ等社交媒体的中小学校班级老师与家长建立的家校群中,经常可见一些家长率先发起某些议题,比如为老师送礼物、赞美老师等,导致其他一些家长在并不情愿但担心不参与会得罪老师的平衡性压力下,被迫同意分摊礼物费用,违心发表祝福话语。当然,这种平衡性、跟随性,也会随着社会主体自主性的增强走向衰减,这也是所谓“00后改造职场”的一个表现。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书中还谈到了社会流动带来的关系信任变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加速推进城市化、工业化,人口流动也从最初的季节性流动转向了更为突出的大规模迁徙,人口越来越突出地集中在大城市。而城市本质上就是陌生人社会,“一切都是暂时的和不可预见的,因此信任的风险也就随时存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必然依托于可追溯、可确认的信任,比如某一类群体之间的信任,结伴同行中的信任,经由稳定交往达成的信任,等等。但这种信任本身也具有突出风险,又或者说某些人通过类似某些社会资本刻意骗取其他人的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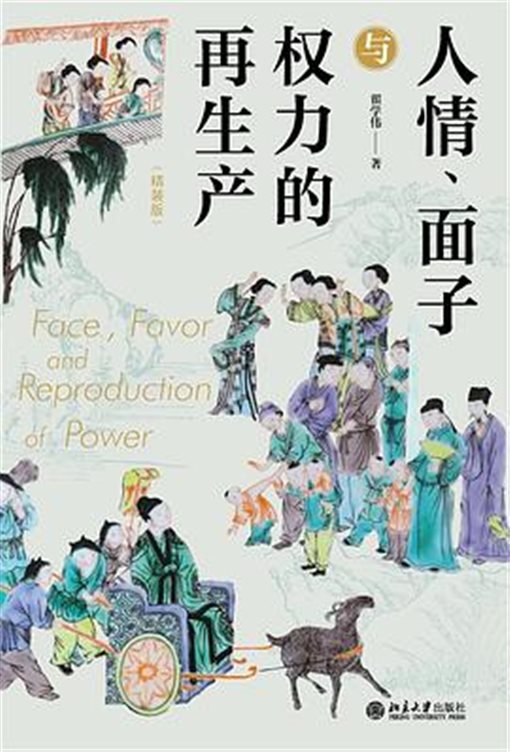
书名:《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作者:翟学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8月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