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名不难看出,儿童文学作家曾志宏的新作《山精灵》是一部幻想作品。在城市里长大的女孩春九,到燕子山的外婆家过暑假,由此展开了一段奇幻的旅程。燕子山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幻想世界,这里住着靠引线穿珠,来掌控四季时序和阴晴变易的精灵婆婆;也有天生一副好嗓门,能在山谷中制造回声的小精灵“呼呼”;还有记录下世间美妙之音、让记忆永固的神奇“录音石”……这是一个亦真亦幻、空灵玄美的所在,阅读《山精灵》,是小读者的想象力被不断激活的过程,他们的心灵会安上一双翅膀,随着山间精灵舞动的身姿,飞向燕子山的山巅,也飞向更辽远的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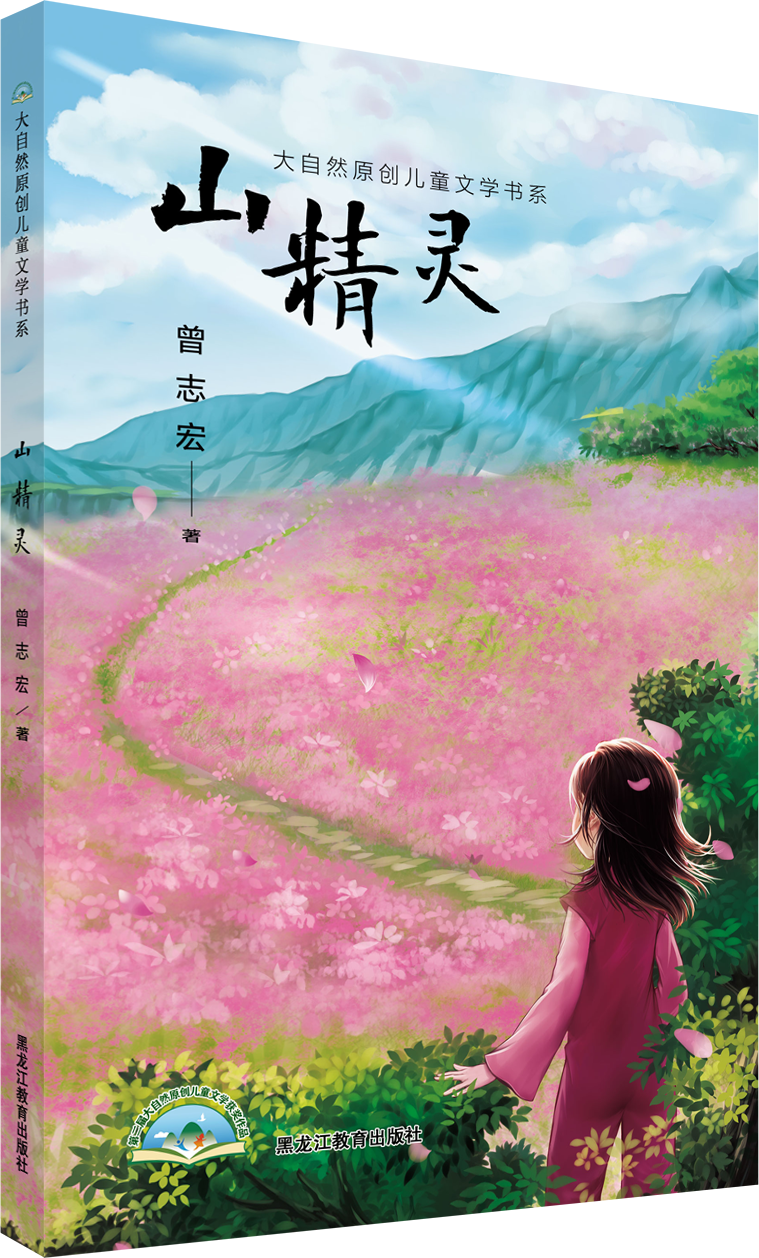
但《山精灵》不是纯粹的虚构,而是从现实出发的一次贴地飞行。
小说有浓浓的现实情愫。它闪耀着亲情的光泽,外婆对春九无微不至的疼爱和照顾,能触动读者内心的柔软之处;作者还在日常生活的片段里,含蕴了时代的波澜壮阔,为小说注入一股淋漓的元气,如舅舅为了推广山里的农产品,摸索着开展直播带货,终于借互联网的东风,让家乡土特产走向千家万户。难能可贵的是,小说还有很好的科普功能,城市里难得一见的蛇莓、马荆花、绿带燕凤蝶、“黑头倌儿”等生灵,兼及猕猴桃的栽种、竹笋的挖法,让小说充盈着清新的山野之气。这是儿童文学的“立人”功能,以审美叙述而非说教灌输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教育任务。《山精灵》为处于精神拔节抽穗期的小读者,提供了相当丰厚的思想营养,它无疑是一部兼具想象之美和教育之用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这还是一部浸润着童年精神的作品。
《山精灵》的故事以春九的视角展开,在春九看来,燕子山的一切都如此神奇,她仰望夜空,想要到银河里去洗澡,想象月亮躺在银河边的吊床上,轻轻摇晃着进入梦乡……这些无拘无束的想象,虽然与现实相去万里,但它有着未经雕琢的素朴,也有着意气骏爽的浪漫,即便是成年读者,读到时都会有被“击中”的感觉。这种被“击中”的感觉,就源于小说内蕴的“童年精神”——所谓“童年精神”,就是“一种原始纯真的思维方式,以幻想、游戏和快乐为内核,呈现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机勃勃的生命情态。”(张国龙:《童话叙事逻辑和中国童年精神建构》)
童年精神是儿童文学的魂和骨。在儿童文学写作中,童年精神不仅体现为一种价值取向,更是一种审美品格。当读者随着春九那天真无邪的目光,看向山间草木,雾霭流云,鸟兽游鱼,当它们纷纷有了生命,翩然起舞,皆成山之精灵时,小说才会变得瑰美而曼妙,轻盈而灵动。
而往深处言之,童年精神不为儿童所独有,而是具有普适性的价值。
对成年人来说,童年精神更是一种稀缺的精神资源。珍重和发扬童年精神,对于重建人本身、以及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曾志宏的巧思就在于,她将生态伦理与自然关怀,作为支撑幻想世界的一根“骨头”,也将其作为建构童年精神的方法与路径。在她的笔下,钟灵毓秀的燕子山不只是春九消磨假日的背景,而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诗学主体,通向童年精神的大境界。曾志宏的写作,这对当下生态题材儿童文学的写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为童年精神安上了一双绿色的翅膀。
小说里,只有春九能看见山精灵,外婆、妈妈、舅舅等成年人都看不见。山精灵为何只是属于春九一个人的秘密?这是一个和原始思维相关的隐喻。古人相信,儿童有“通灵”之能,可以窥见成年人无法看见之物,尤其能通晓阴阳、鬼神之活动。这是因为,儿童多有幻灵思维,相信万物有灵。这种幻灵思维,在人类学上就被称为原始思维,“原始思维又被称为前逻辑思维、神秘的思维、野性的思维、神话思维、隐喻思维、灵感思维等。”(王诺:《原始思维与神话的隐喻》)
这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思维方式。早期人类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便会用鬼神之说,对其进行人格化的理解,这在早期文学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在楚辞里,山中便有着“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的山鬼,水中有“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的湘水女神。这一时期的人类,没有将自然视作外在于自身的客体,而是可以与自身进行精神交感的主体,故而产生了娱神、祭天的民俗传统。它看似蒙昧,却寄托着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敬畏,这是人类童年精神的一大重要面向。
今天的人们,当然不必再用鬼神之说来理解自然。但人心却也发生了异化,小说写到,有一伙工程队,在手续尚未审批完成的情况下,就敢擅自对燕子山动工,肆无忌惮地伐树挖山,这显然是对自然缺乏敬畏之心的后果。人在自然面前显露的贪婪、骄横和暴戾,真可谓触目惊心,这就使得童年精神的缺失,作为一个严峻的命题而被提出。
唯有重新唤醒那颗至臻至美的童心,涤荡人心上的污浊,人才能重建自身,也重建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如何重建童年精神,小说也以文学的方式给出了答案。外婆带着春九上山摘野果,准备回家的时候,春九疑惑道:“树上还有这么多红果子,而且竹篮还空着一半呢”,外婆却回答道,要留些果子给山里的动物,“不能太贪心呐!”这个情节令人心折,不单是因为春九和外婆的对话充满着童真和童趣,也是因为它内嵌着深刻的伦理思索。当人类将草木鸟兽,都视作是和自身一样有生命、有知觉和有灵性的存在,而不是被征服的对象时,以敬畏之心、宽仁之心善待自然生灵,人类才能重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此外,人类诞生于自然,重返自然,就是重返人类的童年,在人与自然的身心交融中,探索建构童年精神的通达之路。
小说着重写了自然对人的疗愈功能。春九领着小姨到大自然中游赏,当她们躺在草地上,全身心地与自然相亲相近时,“春九感觉到自己的耳朵变长了”,她听到了山谷的遥远回响和树叶的哗啦低语。当人与自然彻底融为一体,自然就完成了对人的“净化”,为生活世界的喧嚣所磨蚀的感官被修复,重又恢复了灵敏,即是回到了生命的原初状态。而这种“修复”,不仅是对感官的,更是对精神的——
“小姨身上停了几只蝴蝶,每一只都五彩斑斓,一张一合地扇动着翅膀,小姨简直成了蝴蝶仙子。”这不禁让人想到王维的诗句,“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诗里所用海鸥之典故,乃是说人心纯净,海鸥自与人亲近,人心贪念一起,海鸥便振翅远离。在这里,蝴蝶即是王维诗里的海鸥,蝴蝶落满人身,就昭示着一种趋于理想的、绝假存真的生命情态,它是人类诞生之初,未经世俗驯化的天真和纯良,这是真正的童年精神。曾志宏用她的写作,向我们表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是一条建构童年精神的重要路径,人在与自然的倾心交互中,感官得以复苏,情感得以激活,“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逸兴遄飞之际,进入尼采所说的“酒神状态”,“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尼采:《悲剧的诞生》)。这是一种大境界,人类重新回到孕育自身的自然的子宫之中,童年精神的花圃再度芬芳。
炎夏时节,草木葱茏,《山精灵》的出版恰逢其时,这是一份大自然的清凉邀约,更是给童年精神插上的一双绿色翅膀。当呼呼带着春九御风飞行,“在她们的上方,是明亮清澈的蓝色天空,那么蓝那么干净;远方则是绿油油的山谷,平缓起伏如同滚滚海浪。”这个情节真是美不胜收,它代表着一种指向自由的、审美的存在方式,是人与自然倾心相交后的心游万仞、精骛八极,是童年精神的容光焕发。就让我们乘着童年精神的绿色翅膀,到自然中去,和春九一样,自由而诗意地度过这个暑假,或许,我们也能遇见属于自己的山中精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作者信息:
练韬, 2002年生,福建龙岩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与研究兴趣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有文章见于《文艺报》《长篇小说选刊》《海峡文艺评论》《福建文学》《厦门文学》《中国妇女报》《北京日报》等期刊杂志。
(供稿:王茜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