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与上海和上海人的关系无法切割,在他从路过到定居上海以至终老上海,他的“上海人观”也经历了多次演变,他眼中的上海众生相,折射出他对普通上海市民的深切同情,对不觉悟的小市民的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对两极分裂的文化人的透彻剖析与针砭,以及对压迫者和黑恶势力的揭露与抨击。他的“上海人观”的心理基础和社会意义,在于回击压迫者的文化围剿,揭示时代的众生相,引起疗救的注意,呼唤改造国民性,呼唤新型人格和塑造城市精神品格的理想追求。
——王锡荣,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左翼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

身处上海,鲁迅怎样看上海人?这是他无法回避的问题。从鲁迅一生与上海的关涉,在上海的人生历程,与上海人打交道的体验,以及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鲁迅对上海人观感的演变史及其特点,可以看到鲁迅眼中的“上海人”的整体样貌及其在鲁迅心目中的位置,也可以由此思考鲁迅精神与上海城市精神品格建构的关联。
鲁迅上海人观的心理基础与社会意义
王锡荣
回击压迫者和上海滩黑暗势力的围剿
鲁迅的上海人观,相当程度上是为回击黑暗当局和势力的围剿。鲁迅早年在北京等地,也有对当局的抨击,而在上海则遭受了更严重的压迫,他也参加左翼组织,与其中的战友们并肩抗争,也通过各种文字方式予以回击。由于当时上海是中国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兴城市,聚集了中国最炙手可热的官僚买办、工商企业、经济巨头、权贵门阀,即使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集团人物,也往往在上海活动,他们掌控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鲁迅对“统治者”“压迫者”等权贵阶层的揶揄、抨击、抗争,更多反映在上海的社会背景下。因此,当鲁迅说“统治者”“压迫者”的时候,通常其外在指向为上海的达官贵人和黑暗势力。
例如他1931年说“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首先指上海文艺界的现状,他所说的对左翼文艺界的压迫,首先指上海当局对上海文艺界的压迫,他和左翼战友们所进行的反抗,首先是反抗上海的当局——以陈德征、朱应鹏、范争波等 “政府委员”“侦缉队长”为代表,通过“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类“审查官老爷”,对书店、报刊和作者的打压,联动强力机关,进行查禁、扣押书报刊,查封书店、学校、社团,取缔左翼文化组织,追捕、绑架、关押、枪杀文化人。同时又开书店、办报刊,大造舆论,造谣污蔑,诬陷左翼人士,不一而足,对这些丑类毫不客气地予以抨击,在鲁迅对上海人上海事的议论中在在可见。有时候即使不专指上海的人和事,但在鲁迅话语的语义指向中,仍然不脱这批横行于上海的丑类。鲁迅议论这些人的比重虽然不是最大的,但分量却是最重的。
揭示时代众生相,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鲁迅对于上海人的议论中,揭示黑暗时代众生相,特别是对上海小市民的生活状态的观察,是鲁迅对上海人的议论中最凸显的部分。鲁迅一生关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注重通过自己的文字,“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小说是如此,杂文也是如此,与有人的通信也是如此。无论是写那些无故“吃外国火腿”,被洋人推“落浦”的,无故被巡捕用棍棒敲头,还是那些靠在路边吃侉饼,回家摇着蒲扇乘凉聊天,或者放留声机唱小调、搓麻将吵架的邻居,以及令人讨厌的“阿金”们,鲁迅都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对他们的不幸投以同情的目光,并常为他们鸣不平,而对他们的麻木、愚昧和甘于现况,则予以批评和针砭。
鲁迅很清楚,这些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精神积淀所造成的,既有根深蒂固的传统积弊,也有伴随西方船坚炮利一同舶来的精神麻醉。上海仍满街是早前发现的“万难打破的铁屋子”里由昏睡而行将死灭的人们,所以,他不恤让自己成为夜间啸叫的不祥之鸟,发出尖利的哪怕是不入耳的警告,希望警醒铁屋中的人们,从而一起来打破这铁屋子。
其中,鲁迅针砭最多的是知识分子。也许是出于对自身所属的社会阶层社会责任所在的观察与思考更深入,对其与生俱来的缺陷与弊病,以及时代的熔化与毒化作用,看得更真切,故指陈更加痛切,解剖更深透,更不留情面,也不惜用最锋利的言辞予以指斥,因此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更丑陋的一面,并引起思考:从上海的知识分子看中国,他们身负何种使命,他们能否担当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他们的堕落给时代和社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又何以自救?与其说鲁迅对知识分子种种弊病的揭示是为了使之出丑或被赶下社会舞台,不如说他是一种呼号和警示,揭露这些不忍直视的丑陋之处,为的还是引起疗救的注意,引起知识分子自身自救的自觉和社会刮骨疗伤的主动。比如鲁迅谈到那些诬称内山完造为日本间谍的人们:“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虽然已经“狗也不如”了,但最后不还是落在要他们“学”上吗?这就仍然存着要“救”他们的期望和希望他们自救的意涵。
呼唤新型人格和塑造城市精神品格
尽管鲁迅对上海人有种种不满的表示,甚至对一些他目为败类的人有严厉的痛斥,但严格来说,这些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而在另一个侧面,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鲁迅对上海人也有肯定、赞扬、期待和提倡。
就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而论,其中说了“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不仅其能指本身就涵盖上海人,而且看后面的所指就可以知道,主要是说上海的革命者:“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之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正如鲁迅经常说的,在上海看到很多优秀的青年被捕并就此失踪,因此,“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地底下”,就是先烈,就是“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之中”的人们,例如左联五烈士。中国人的自信力究竟有没有,只要看看地底下这些英烈,联想他们的精神,就会昭然若揭。这些是鲁迅通篇文章立论的事实基础,也是其基本逻辑。
1933年2月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说:“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而在1934年10月鲁迅就在“记起他们,再说他们”了,并且让人联想到他们的有确信、不自欺,前仆后继地战斗而被摧残、抹杀、消灭于黑暗中,所以已经在“地底下”。鲁迅要看的“地底下”,无疑指向包括他们在内的先烈们。虽然他们也都不是上海当地人,但是无疑已经都融入上海这个城市的血脉,而且成为构成上海城市精神与品格的精粹。
在这里,鲁迅所称扬的先烈们的精神——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有确信、不自欺,前仆后继战斗,正是左联五烈士及其战友们的可贵精神的写照,也是上海这座英雄城市的城市精神与品格的精髓。
结语
鲁迅的上海人观,其内在逻辑始终是爱国与强国。从这个视角回看鲁迅对于上海人的种种议论、批评、指摘、讥刺甚至痛斥,以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真正的心理基础和出发点,则是恨铁不成钢,是寄希望于通过这些苦口良药,能让那些迷茫的、盲目自信的、自迷于可怜的优越感的上海人幡然醒悟,抛弃那些盲目的固有观念,“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改造扭曲的国民性,建立新的足以配得上第三样时代要求的人格与城市精神品格,这也就是鲁迅一生追求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的愿景。
新书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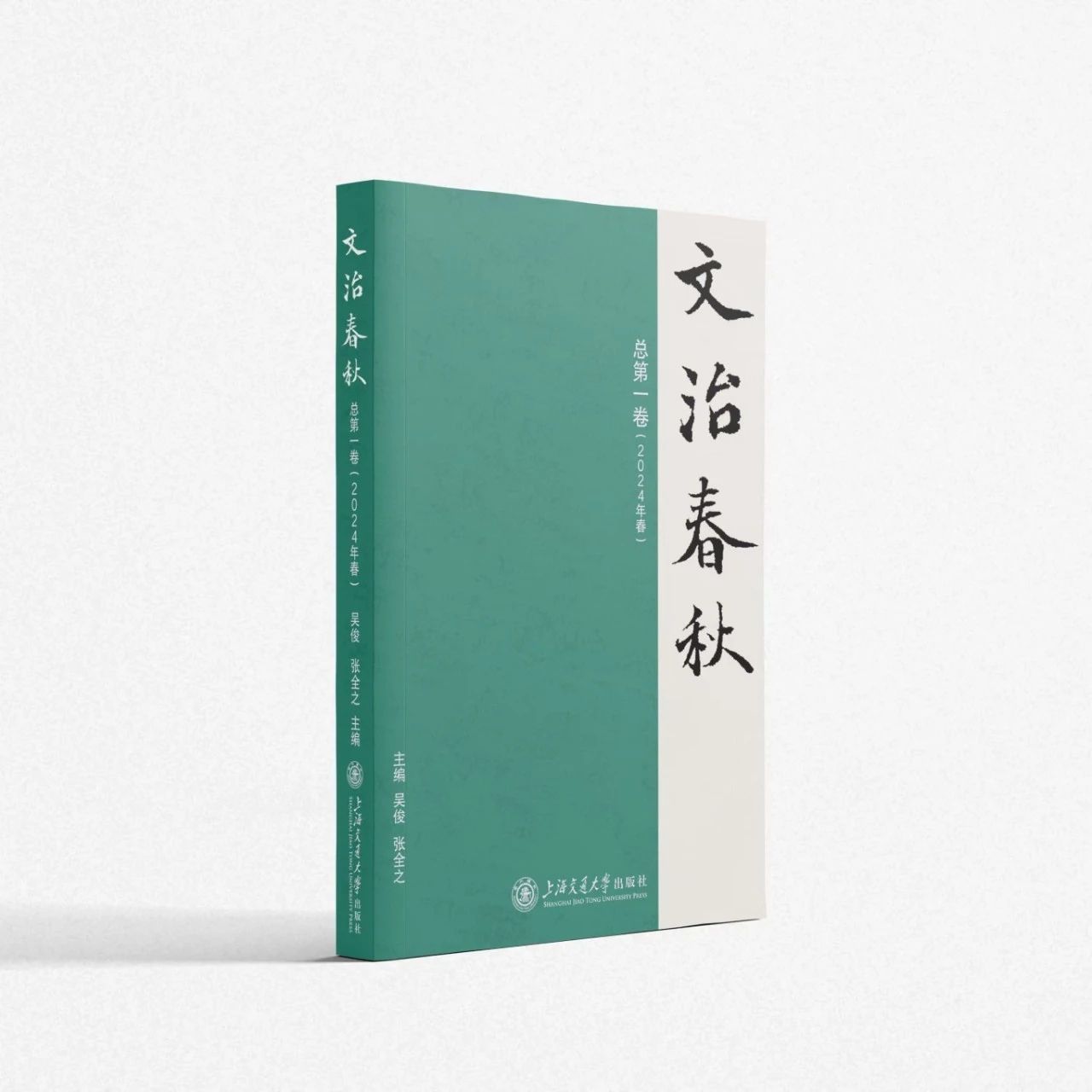
《文治春秋 总第一卷(2024年春)》吴俊 张全之 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图文源自本社已出版图书《文治春秋 总第一卷(2024年春)》,篇幅有限有删减)
(供稿:张丽霞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