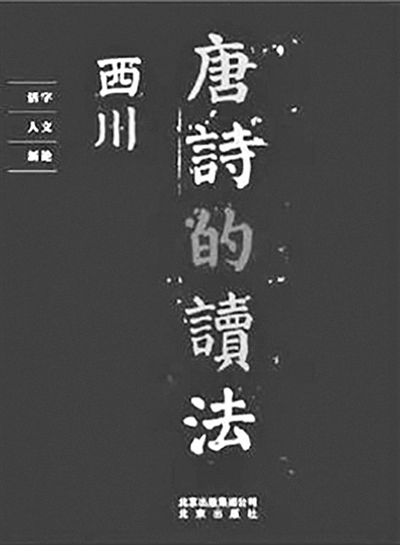 |
| 《唐诗的读法》西川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4月版/45.00元 |
今年4月,诗人西川的《唐诗的读法》一书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然而其主要内容早已刊于《十月》2016年第6期,甫一刊出,就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不少讨论。而备受争议的“唐代为其诗歌成就付出了没有大思想家的代价”的观点也早在他早期著作《大河拐大弯》里提了出来,至于唐人作诗打小抄的轶事,更是一时哗然。然而笔者认为,这些所谓“对话”与“争论”,未免更像是“误读”。
正如西川所说,如今人们习惯于“把唐诗封入了神龛”“供起来读”,来获得一种“文化身份感”。联想到当下的“国学热”和“诗词热”,这种批评可谓相当尖锐。他指出,现代人“大规模缩小对唐人的阅读”,只拿一部等同于儿童读物的《唐诗三百首》来读,把唐诗局限在一些“道德正确、用语平易且美好”的代表作中,这种读法无疑是以偏概全,如入宝山而空手回。用西川的比方来说,“若以为熟读唐诗三百首就向唐朝看齐了,就相当于我们去曲阜旅游了一圈(还参加了当地的祭孔大典),就觉得自己接续上了儒家道统。”
诚然,我们可以说某个诗人、地域或时代的代表作如何如何,但这些“代表作”往往并不足以覆盖诗人、地域或时代的全部侧面。从这点上来看,寒山和王梵志,或许正是给浅阅读的读者的“一服清醒剂”。只有告别浅阅读,我们才会意识到,“写诗是唐朝文化人的生活方式”,“是发现、塑造甚至发明这个世界”,甚至这种生活方式渗透到民间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工匠或文人,才塑造成这样一个黄金时代。诗歌反映着古人的真实生活,既有隐逸的情调与豪迈的气概,也有文以载道的抱负与忧国忧民的情怀,而绝非仅是单纯的附庸风雅,也不是浅尝辄止的文化味精。
在当代语境里,诗从来只在“远方”,并不在直面生活的杜甫那里,更不在笃志传道的韩愈那里。对今人而言,杜甫和韩愈显然是陌生的,他们不同于那些容易“舒服接纳的美文学”,不同于“周作人、林语堂、张中行化了的、晚明小品化了的、徐志摩化了的、以泰戈尔为名义的冰心化了的、张爱玲化了的文学趣味”,他们独特得无法被今人接受,更无法被当作今人想象的“唐诗”来接受。
这样的浅阅读,虽然也观照到了唐诗被选本遮蔽了的一面,但却“浅”在了理解深度上,其实低估了这些大作家们原有的价值。这种读法固然有补偏救弊之功,但当时诗人是要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相抗衡,而到了今日,载道与言志的对立失去了土壤,人们“无道可明,只好认‘诗言志’为最高写作纲领”,从而彻底忽视杜甫的沉郁诗风与儒家情怀、韩愈的奇崛拗硬与儒家担当。西川不无痛心地认为,我们的文化中若没有这种厚重与伟大,“没有这样的庞然大物镇着,我们轻浮起来就会毫无底线”。
当然,西川不是要为儒家情怀招魂,只是要读者注意“知其人”“论其世”。尽管过去一个世纪新批评与结构主义在文学研究中大行其道,但回归文本并不意味着完全割弃作者与时代,尤其是产生于“知人论世”传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如果抛弃历史的眼光,把文学当成与时代隔绝的永恒存在,那无疑是偏颇的。
就像西川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我不愿意让古典的东西蒙上尘土。”而西川要做的,就是为唐诗“刮垢磨光”,恢复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解释学,驱散今人眼中蒙住唐诗的尘与雾,破除浅阅读带来的片面认识,让唐诗回到历史现场中放出应有的光来,再照进我们当下的写作,而这或许就是《唐诗的读法》最大的意义。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