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登基,国号为汉,后人称为蜀汉、季汉。当时,就像是曹丕登基前,中原地区涌现出大量祥瑞一样,巴蜀地区也出现了各种异象,来佐证刘备登基的合理性。
刘备军政集团当时还编造了曹丕杀害汉献帝的谣言,因为只有那样,才能指控汉献帝禅让帝位的做法、曹魏王朝的统治不具法理性。
但即便如此,刘备的汉室继承人仍然十分牵强,因为作为汉景帝旁支的后裔,在血统上,刘备与汉献帝一脉相去甚远。而且,季汉只占据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重庆全境,以及云南、贵州、陕西、湖北的少部分地区,距离传统意义上的华夏中原很远。
所以,笔者能够理解新出版的《三国:英雄、江山与权谋》书作者所称的刘备称帝旨在满足自己的私欲,对于整个集团没有什么好处,也难以团结真正意义上的汉室遗老的结论。
但刘备当时的选择其实也多少有些无奈。刘备军政集团的骨干精英,相继老去或战死,所剩不过诸葛亮张飞寥寥几人,刘备自己年岁已高。这种情况下,如果刘备死去,他的幼子在没有一个王朝、帝位作为笼络的情况下,将难以维持集团的基本盘。一个王朝之中,权臣夺位被称为篡位,就像是曹丕代汉一般被描述为曹丕篡汉,但普通的军政集团发生权力更迭,似乎就没有道德上的太多束缚,历史上并没有太多人指责比如朱元璋篡夺了他名义上的主公的家业。
而且,就像是《三国:英雄、江山与权谋》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刘备自己心里很清楚,虽然他将曹丕代汉说成是篡汉,还渲染曹丕杀害了汉献帝,但汉室在中原地区从世家豪门到普通民众确实没有太多人拥戴,被替代以后如果没有军政集团继续打出汉室的旗号,汉室就不可能再有复兴的可能——东吴的孙权,在曹丕称帝后就接受了曹魏给予的吴王封号。
这种情况下,当刘备准备举兵向东吴复仇,一雪荆州被袭、关羽被杀之耻时,发生了张飞被杀的恶性事件,就更显蹊跷了。历史记载张飞酒后鞭挞下属,以至张达、范强将其杀害,还带着张飞的首级去了东吴。张飞当时是新建立的季汉的二号人物,政治地位高于其他大臣,且在阆中整军准备东征孙吴,大营防备显然会强于平时。这种情况下,两个下属能够轻而易举地、悄无声息地杀死张飞,然后带走首级,还畅通无阻地逃到东吴,是难以让人理解的。
刘备更加狂怒,但从其领军讨伐东吴的进军进程来看,他其实在221年7月到222年的夏天多次往来永安和夷陵之间,并没有下决心猛攻东吴控制下的城池。其举动更像是胁迫东吴拿出更为有利的议和条件,在陆逊有意的诱导下,甚至摆出了数百里连绵扎营的阵势。接下来,就是火烧连营的著名故事了,然后,刘备白帝城托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夷陵之战虽然是季汉立国以后最耻辱的战役,但与季汉一道丧失了战略机遇的还有曹魏。在季汉跟东吴对峙期间,孙权对曹魏多次委曲求全,说尽软话,甚至不惜派遣自己的太子到曹魏为质子。因为这时如果曹魏出兵,东吴的世家大族很可能会研判无力同时对抗季汉和曹魏两家,而选择对实力最强的曹魏投降,世家甚至可能将孙权一家绑缚了送到洛阳去。
事实上,曹丕当时也曾收到过大臣的建议,但本着吃瓜第一的精神,只看刘备跟孙权在夷陵对峙以至大打出手,而没有乘势伐吴或者讨伐季汉。反倒是刘备病逝后,诸葛亮主持大局与东吴重新修好,曹丕才开始带兵南下,但因为已经错失良机。
公元222、224、225年,曹丕在位才短短几年,就三次征吴,都换得草草收兵。而在此之后,曹魏与东吴之间多次交战,通常都是以发起进攻的一方败退,对峙之势变得十分明朗。
丢弃荆州,再加上夷陵打败,季汉的国力在三国之中位居末位。但如《三国:英雄、江山与权谋》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越是这样,因为季汉立国的法理性问题,再加上外来士族与益州本地士族之间的矛盾,就越需要将矛盾和斗争对外输出。
书中其实说得很明白,季汉的国力支撑不起大规模战争、持续作战,更不能被动等待与曹魏之间的国力竞争,所以只能北伐,通过夺取曹魏的部分区域和人口来试图逆转局面——这一选择的成功率并不高,“凭诸葛亮的才能,这些问题他应该都考虑到了。但他还是坚持出兵,因为他的国家已经站在悬崖边上,没有退路了。他只能主动出击,以呕心沥血的姿态,凭借自己的才干,去寻找那一点点微渺的破局希望。”
“这是一次飞蛾扑火似的尝试,前面的道路注定无比坎坷,需要诸葛亮以毕生鲜血去填补沿途的沟渠。但他义无反顾”,这既是对于刘备个人三顾茅庐、白帝城托孤的巨大信任的报答,更是对汉室复兴理想的一次争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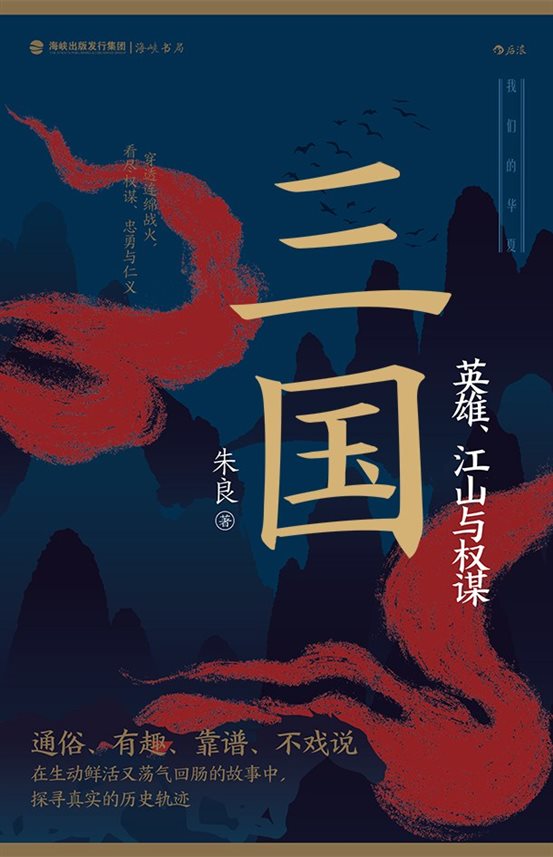
书名:《三国:英雄、江山与权谋》
作者:朱良
出版社:海峡书局·后浪
出版日期:2023年9月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