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对于苏格拉底的认知和印象,主要来源于他的学生柏拉图。柏拉图在撰写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记录以及与他自己的早期对话时,比较精确地予以了再现。
20世纪和本世纪初最为重要的知识分子、当代著名历史学者保罗·约翰逊在其所著的《苏格拉底:我们的同时代人》书中指出,但柏拉图不仅仅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而且还开宗立派,在雅典的城郊公园里建立了研究机构“阿加德米学园”(Academy),“学院”(academy)之名就源于此。这也可以被视为最早的大学。这个学园最为优秀而著名的校友就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后者又创建了自己的大学吕克昂。
按照保罗·约翰逊的看法,阿加德米学园与吕克昂的关系就像是近代以后很多保持学术交流与合作,但彼此维持竞争的大学之间的关系。
书中指出,柏拉图经营学园,开始系统地阐释他自己的理念,将之融入一个体系,并因此改变了对苏格拉底的塑造。所以,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后期的描绘中,成为了“一个能言善辩的玩偶”,服务于柏拉图哲学传播。
保罗·约翰逊认为,这就是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谋杀”,造成了苏格拉底的第二次“死亡”,“将一个充满活力、基于史实的思想家转变为一个会说话却没有头脑的玩偶”。
当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同时代人,还提供了其他一些有关苏格拉底的信息。比如曾经撰写过对苏格拉底颇具敌意的戏剧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此外还能从西塞罗、普罗塔克、圣奥古斯丁、德尔图良等众多古典作家与中世纪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一些有关苏格拉底的逸闻、概要、语录与信息片段。
所以,《苏格拉底:我们的同时代人》力图从柏拉图后期作品制造的迷雾和疑云中,重新找出属于苏格拉底自己的有用信息。
如书中所梳理指出的那样,苏格拉底成长于民主城邦雅典,他本人曾经是一个坚毅的军人。日后的伟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比苏格拉底小10岁,也曾受到过后者的影响。按照苏格拉底年轻的贵族朋友阿尔西比亚德的说法,苏格拉底在46岁时仍然完整地佩戴着盔甲并携带武器,奋力杀敌,让敌人望而生畏;而且,苏格拉底冬天身着单薄,甚至在雪地上赤足行走。按照史籍记载,苏格拉底在世时经历过不止一次的瘟疫,但这对于他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苏格拉底相貌丑陋,脸上长满胡子,头发茂密,有着又大又扁的鼻子,引人注目的突出眼球,嘴唇肥厚。到了老年,他还大腹便便。但他丝毫不以为意,经常用反讽的口气与他人辩论。有时,在街上,别人嘲笑甚至推搡他,他也不生气,旁人询问,他就说,“倘若一头驴踢了你一脚,你会起诉这头驴吗?”“倘若一个人扇了我一耳光,他并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伤害,这仅仅有损于他自己。”
苏格拉底50岁后才娶了一个叫做克珊西普的女人,生了三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因为过于年幼甚至是在苏格拉底被处死的前夜,还被母亲带着在牢房里跟父亲共度。很多资料都将克珊西普塑造为一个泼妇,经常呵斥苏格拉底。但他还是不生气,以一种用现代眼光来看颇有些性别歧视观念的话来调侃,“因为我们从驯马的行业中可以得知,主人经常喜欢挑选一匹难以相处的动物,它们会产生更为有趣的问题”。克珊西普显然不吃苏格拉底的幽默那一套,会从房顶将一盆污水泼到苏格拉底的头上,后者就会说,“正如往常一样,紧接着雷鸣的就是暴雨倾盆”。
《苏格拉底:我们的同时代人》书中讨论了苏格拉底时代雅典城邦从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由盛转衰的过程。毫无疑问,与文明史上其他很多帝国、城邦文明的衰落方式相同,瘟疫导致了雅典大伤元气,而这甚至被当时的人们解读为因为雅典人过于渎神所以招致了可怕的结果。而雅典城邦的霸权也走向衰落,这似乎也证明了渎神的可怕。
在那样一个充斥着迷惘的时代,雅典等希腊城邦涌现出很多哲学家、诡辩家和科学家。而苏格拉底毫无疑问是最独特的一个,他热衷在集市中行走,与完全没有机会进入政治领域、缺乏哲学修辞训练的大众对话,提出问题,思考回答。这当然是一种完善智识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其实展现了一种在古代罕见的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
他不断询问包括贸易、职业以及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求出答案,然后接着询问。如书中所说,这不仅仅使得苏格拉底本人获得了更多的智识,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的追问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督促,使得人们可以“孕育出在他们的头脑和心灵中已经拥有的真理”。
《苏格拉底:我们的同时代人》这本书指出,苏格拉底一次次通过追问、反诘证明,无论是宏大的主题还是一般的命题,“被广为接受的意见不仅几乎总是有缺陷的,而且经常是完全错误的”。而柏拉图试图建立起的绝对主义的城邦,一个依靠哲学建立统治的国度,恰恰与苏格拉底的思索是完全违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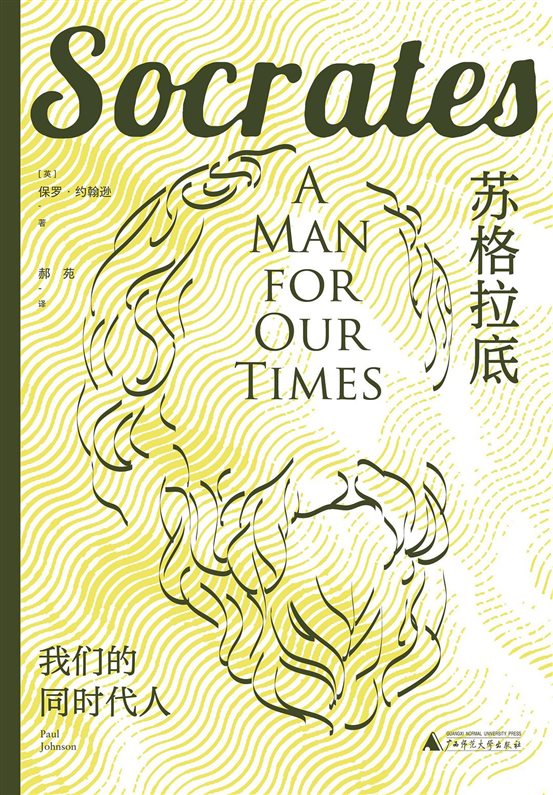
书名:《苏格拉底:我们的同时代人》
作者:(英)保罗·约翰逊
译者:郝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9月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