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历史学家王寿南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台湾中国历史学会理事长。王寿南所著的《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一书,纳入数据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中国唐代中后期藩镇与中央关系,包括唐政府对藩镇的控制、藩镇拥兵自重及其对地方的控制方式、藩镇军力与唐政府控制力之间的此消彼长、唐政府与藩镇之间的经济关系、河北三镇独立性的文化因素,并分析了唐政府在藩镇治理上的态度和策略。
中国唐代中后期的藩镇割据,以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分立、战乱乱象,极大地透支了唐帝国中前期的政治资源、制度活性。这之后建立的宋朝,对于武人集团始终予以制度化的排斥和防范,以不惜大大降低军事行动效能为代价来削除武将格局的隐患风险。
唐朝初年,国势鼎盛,在沿边设立了安西、北庭、燕然、单于、安东、安南六个都护府,而在睿宗以后,东、北、西邻国日强,所以又设立了十大节度使。安史之乱之前,节度使均在边境,目的十防范外患。而在安史之乱期间,国内成为战场,为了守护京师以及江淮财税要害地区,唐政府在内陆重要地区也设立了节度使。
《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这本书的一大特点就在于,资料扎实,书作者通过对唐朝藩镇史料记载的各类情况,如不同时期、唐天子任内对唐政府中央的态度等,进行了细致量化。量化分析就非常清楚地揭示指出,唐朝中后期,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跋扈、叛逆的藩镇较多,但这种表现显然具有滞后性,如宪宗一朝对跋扈、叛逆藩镇多采取武力打击的态度,但由此换来的藩镇恭顺则主要体现在随后的穆宗年间,
总的来说,藩镇如果出现一人、一家久任的状况,通常就表示中央对藩镇控制力走向削弱,由野心者乘机倔强跋扈。而黄巢之变后,唐中央政府的权威大幅瓦解,这使得藩镇甚至反过来钳制朝廷,朝廷任免宰相也需要经过藩镇认可。
藩镇之所以在唐朝中后期成为严重的政治军事问题,跟唐代的府兵制走向衰败有关。府兵制在高宗以后,其制度就慢慢被破坏,这使得府兵这一朝廷直接统属的职业军人阶层,解体而取而代之为边地镇兵为主体的新军人阶层——后者则完整意义上成为了地方统属,后来异化为藩镇一人、一家所属的私兵集团。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安史之乱期间,为了平息军力强悍的叛军,提高军政运转效率,唐政府不得不下放了许多原属中央的权限,尤其是对基层官吏 监察权,还有荐举、考第之权。后来,藩镇更加架空了朝廷对藩镇下属州县的课税的权力,而这为其成功实施割据提供了财力支撑。
宋代,欧阳修曾说过,“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亡于乱也”。意思是说,唐朝中后期,兵力分散在藩镇,原本是为了拱卫国家,抵御外患,但拥有强盛兵力的藩镇反而成为了战乱之源;这种混乱进一步刺激了藩镇扩兵。对于这种情况,唐政府往往也只能追认拥有武力的藩镇之中的权斗结果、扩军事实,乃至藩镇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大打出手的局面。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宦官对唐政府中央禁军的掌控,这其实意味着唐朝皇帝以及文官集团同时失去了对中央禁军和藩镇的控制。中央禁军沦为宦官私兵以后,战斗力变得更差,这使之也不能达到震慑藩镇的目的。
因此,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中,唐朝中后期的诸位皇帝,通常必须小心地在藩镇与藩镇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对于那些完全不将唐朝天子和政府当回事的藩镇,通常利用各种方式诱引起周边其他藩镇出兵干预。
诸多的藩镇,过度的横征暴敛,这一切正是唐朝晚期各路盗贼、民众反抗掀起的根本原因。而民众反抗浪潮显然具有跨区域性,不可能仅仅限于一家或几家藩镇。而这种反抗当然会破坏当地的农业经济和贸易发展,造成税源流失,藩镇会因此继续加大对属地臣民的盘剥。
《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书中也谈到,安史之乱成为唐朝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发展局面由盛转衰的关键点,这之后,江淮及其以南地区逐渐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中心区,替代关中和中原。江淮地区的藩镇,总体上对于唐朝政府的支持、忠诚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藩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江淮地区藩镇多由朝廷选派文官以执掌的因素相关。
书作者还提到,藩镇割据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动机,那就是自保。无论是当时由朝廷选派,经过正规人事程序商人的藩镇将领,还是通过手下人推举、上任藩镇子嗣继承等方式产生的藩镇主官,都必须尽快聚拢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才能做到基本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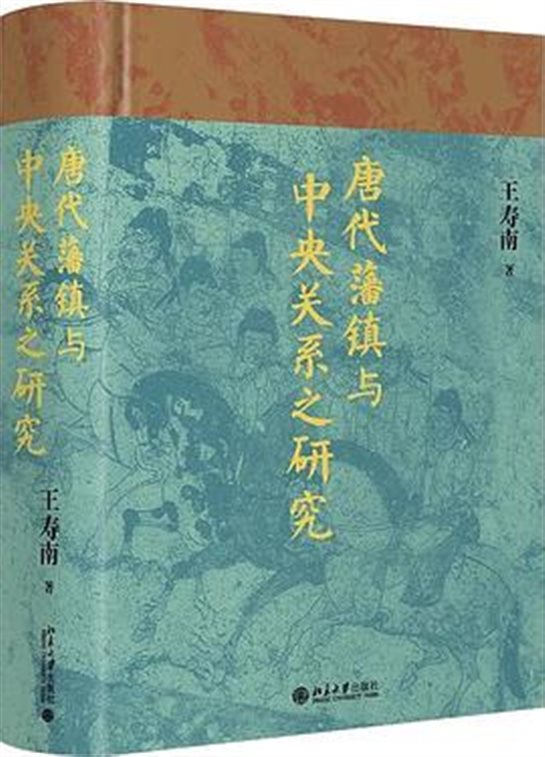
书名:《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
作者:王寿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10月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