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历史学家、都柏林三一学院历史学博士约翰·吉布尼撰写的《爱尔兰简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书中谈到,17世纪初,“爱尔兰以毁灭性的方式”被英格兰彻底征服——征服战争期间,英格兰采取了非常野蛮粗暴的方式,让爱尔兰城镇体系几乎都变成了焦炭化的存在。
这之后的三个多世纪,英国一直都努力整合爱尔兰,但在19世纪,这番努力其实已基本上宣告失败。正如《爱尔兰简史》书中所说,英国通过取消通过取消爱尔兰的关税壁垒,设法击溃了爱尔兰的羊毛、棉花行业,为英国本土的产业让路。
更重要的危机在于,19世纪40-50年代,爱尔兰爆发严重饥荒,但英国当局在饥荒爆发后仍将爱尔兰的大量粮食出口,这就造成爱尔兰人口出现了百万数级的减员(1845年爱尔兰人口为850万,19世纪50年代则降到了650万)。
爱尔兰大饥荒使得很多当地人无奈选择移民,除了移入英国其他板块的,就主要去往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书《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这本书出自爱尔兰历史学家、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奇安·T.麦克马洪。书作者通过梳理欧洲、北美、澳洲三大洲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探寻了19世纪中叶爱尔兰移民逃离家园,而在海上遭遇各种风险甚至是致命危机的经过。
正如书作者所说,大饥荒中的爱尔兰难民忍受着长途旅行带来的种种风险,很多人拼尽全力才筹集去往新国度的船票费用,在路途中不得不忍饥挨饿。爱尔兰难民当时很多人选择的是从北美、澳洲运送货物到英国并在回程空舱的船只,这也意味着当时的航程相较于乘坐客舱轮船旅行更加危险,基本上没有舒适性可言。
《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全书开篇讨论的是爱尔兰难民筹集旅费的艰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爱尔兰农业在当时歉收,所以地主根本不愁招录到相对更少的佃农,甚至有意愿赞助那些愿意离开爱尔兰而到别的大洲或英国本土谋生的离开者。书中也谈到,英国政府当时对于爱尔兰问题的态度也颇为暧昧,一些情况下也为移民提供了部分资助。
通常而言,爱尔兰移民、难民当时选择的目的地,一般会考虑自己亲属、乡亲的移居地。当然,这也必然意味着移民的目的地选择,很多情况下带有偶然性和随意性,也使得英国、爱尔兰开往北美和澳洲的船只,在一些时候不能恰好对应移民的目的地需求的情况下,或者移民自身的法律问题没解决好的情况下,就会造成滞留。
好不容易得以出发,更直接的挑战在于,从英国、爱尔兰去往北美和澳洲,尤其是澳洲,航程非常遥远。如书中所说的那样,很多乘客很难适应海上生活带来的种种挑战,除了晕船,还有就是睡在货船木制货架上的巨大不适。英国当时依旧奉行对送往澳洲的移民船只的严厉法律,因为最初的澳洲移民本来就是罪犯。但换到了爱尔兰平民以难民、移民身份乘坐这些船只,就显露出管制规定与纪律的呆板和粗暴。《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书中谈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乘客开始发展出与同船相同身份的他人的友谊,某种意义上发展出所谓的“情感共同体”。
更严峻的挑战在于,爱尔兰人当时乘坐的船只大多是货船,这类船只本来就不配置医生,因而漫长旅程中,一旦罹患疾病,以及更为普遍和常见的营养不良和虚弱无力,就有很高的概率出现生命危险。书中援引史料分析指出,当时的爱尔兰移民旅途中的死亡率在10%-20%之间,这个死亡率肯定要大大低于更早以前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向美洲贩卖黑人奴隶所造成的死亡,却也显著高于正常长途洲际旅行的死亡率。
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爱尔兰是天主教国家,人们普遍高度重视宗教仪式,包括丧葬习俗,以此表示对死者和临终者的尊重与关怀,但大饥荒时期,爱尔兰人已经无暇顾及这些仪式,人们长期坚守的仪式至此发生了比较突出的撕裂。而在船上,死者甚至会被绑上沉重的金属片,然后丢弃到海中——这些做法对于生者在精神上构成巨大的煎熬。
所以,当时的移民船上,“数以百计的穷人、男女老少,从90岁的老年痴呆者到刚出生的婴儿,都挤在一起。没有光,没有空气,在污秽中打滚,呼吸着恶臭的空气,身体抱恙,精神萎靡”。这样的现存状态一遍又一遍地提示着幸存者必须谨记脆弱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中期运送爱尔兰难民、移民的船只,被称之为“棺材船”——管材和船这两个词汇的搭配,简洁地概括出了过高死亡率和大规模移民,而这作为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整体记忆被稳固地嵌入了爱尔兰人的思维体系。
所评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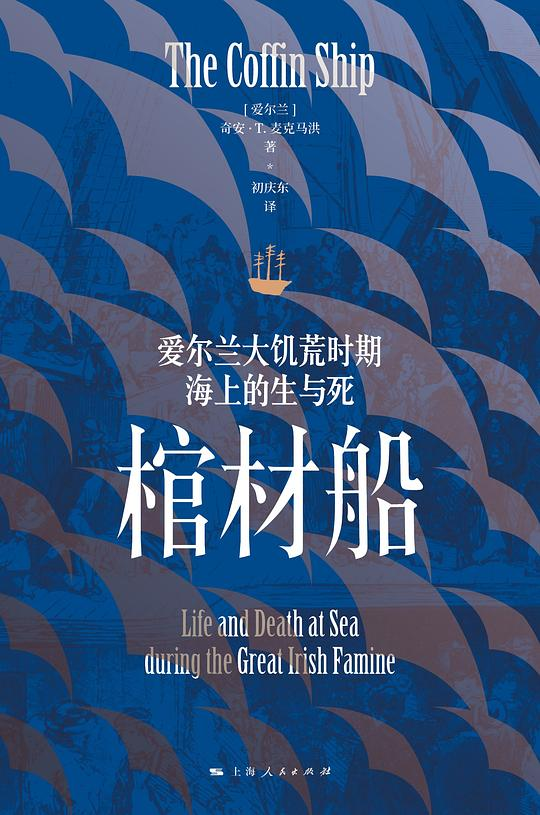
书名:《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
作者:(爱尔兰)奇安·T.麦克马洪
译者:初庆东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3月
供稿人:陈 麟
初审:戴佳运
复审:陈 麟
终审:张维特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