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儒家、儒学?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与研究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竞恒所著的《爱有差等:先秦儒家与华夏制度文明的构建》一书,对此给予了一个不一样的定位。
按照书作者的看法,“儒学是鼓励平民模仿做贵族的学问”。中国历史上有两波贵族社会瓦解和进入平民社会的浪潮,第一次是春秋晚期到秦汉早期,第二波就是唐朝末年到北宋末期。
汉朝成长起来的贵族士族,也就是后来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唐朝的世家大族,其实是汉代儒学重建社会,从平民精英中新造出来的。书作者指出,汉儒对于社会的重建,就是鼓励平民精英模仿早期的周朝贵族,以孔子所说的周礼来让宗族覆盖到乡里,使之具有一定的自组织能力。这对于秦政一方面起到了解构作用,也就是皇权虽然名义上是至高无上的,但在郡县以下,实际上不得不依赖于士族豪族的帮忙。但另一方面,也真正意义上稳定了秦政。
书作者揭示指出,春秋晚期,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老牌贵族家庭没落,依照军功、经商、做官而崛起的平民精英,逐渐开始承担起过去的贵族承担的政治、文化责任。孔子打破过去局限在贵族圈的教育模式,不论出身教授弟子,因材施教,这本质上就是将贵族的教育方式、知识生产过程与传续方式都传授给这些新贵,覆盖面甚至包括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子弟。“(这就)重建了华夏民族的造血机制,从平民中不断造出新的贵族,他们掌握着组建小共同体和进行地方治理的能力,这样再混乱,社会也不会解体”,也不会倒退回到蛮荒时代(然后循环往复早期文明野蛮征战的进程)。
可以说,孔子、儒学之所以伟大,就是使得中华文明得以摆脱了其他很多文明在早期发展向着稳定器转型过程的致命陷阱。书作者说,孔子将平民精英与贵族的融合,“正是托克维尔所赞许的英国社会平民中产阶级与贵族联合起来”,并不断赋予贵族文化以开放性特质。
西汉时期,儒者重建社会,弥合平民与贵族,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平民获得了姓氏。汉朝忽然出现的鞠氏、濮阳氏、沐氏、薄氏、博氏、郭氏等,都出自秦朝平民家庭,在汉代自己搞出姓氏,并发展为世家大族。西汉中期,平民普遍有了姓,而姓的普及,这对于族的建立(重建)意义至关重要。西汉晚期,很多平民士兵的名字已经很具现代感了,比如李延寿、周万年、赵延年、张彭祖、周千秋等。相较而言,在秦代,平民子弟入伍,普遍没有姓。
欧洲、日本和朝鲜平民普遍获得姓氏,就要晚得多,甚至迟至十九世纪。书作者举例说,在德国,一些平民在十九世纪随意地拿自己从事的职业为姓,比如muller是磨坊主,Schmidt是铁匠,schneider是裁缝,fisher是渔夫,weber是纺织工等。日本平民获得姓,更是延迟到了19世纪70年代,而且也很随意地造姓,比如住井边的叫井上,住在山边的叫山口,养狗的叫犬养,田边有水池的叫池田。朝鲜平民获得姓,是在1909年。
放眼世界,在近代以前,世界各地的平民很少具有姓氏,只有贵族因为需要构建家族文化、家谱,才设立姓氏。平民则一般只有名,就能够满足国家和贵族管理的需要。书作者指出,中国汉代就让平民有了姓氏,就是因为汉儒重建社会,使得平民接纳贵族文化,使得民间具备了小共同体的自组织资源。
书作者指出,中国平民不仅人人有姓氏,重视家庭价值、喜欢传宗接代、喜欢搞家谱。这种做法曾在近代让一些启蒙知识分子觉得落后,但实际上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平民的这些趣味具有非常贵族化的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领先性和独特性。因为在同期的世界其他地方,甚至更晚的其他地方,只有贵族一般才建立了家谱。
有了家族、家谱的概念,平民子弟中涌现的精英,往往也会仿效过去的贵族那样,一定程度上让自己的家传、家谱神圣化。到了宋代,宋儒甚至鼓励平民可以祭祀五代以来的祖先,“普通的中国人潜意识中都以贵族标准要求自己,给父母立墓碑上,使用‘先妣先考’这种殷周时代商王、周王、大贵族才使用的称呼”。
所评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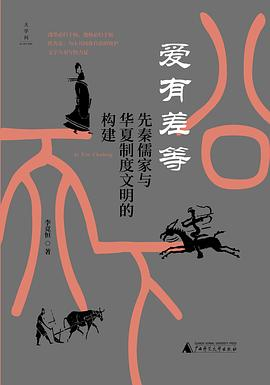
书名:《爱有差等:先秦儒家与华夏制度文明的构建》
作者:李竞恒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6月
供稿人:陈 麟
初审:戴佳运
复审:陈 麟
终审:张维特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