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是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形成的。1963年,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浙江选择诸暨、萧山、上虞等县作为“社教”试点。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经过集体讨论,决定采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对“四类分子”进行改造。这项经验经由公安部汇报后,被概括为“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2003年,浙江省“枫桥经验”纪念四十周年大会召开。十八大以后,“枫桥经验”的坚持和发展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
“枫桥经验”的内核其实就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
新出版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发展与理论构建》一书,刊录了2023年11月23日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理论研究会上的多篇专文。全书分为四编,从营商环境保障、多元参与共治、民事司法完善、机制创新审思四个方面展开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不同面向,具体覆盖了讼源治理、多元解纷、基层治理等不同话题,结合了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小额诉讼等多项制度,对“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呈现状态、发展路向进行了深刻归结和展望。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其才在《“枫桥经验”与发挥村规民约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作用》一文中讨论了,如何有效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针,更好地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尤其是矛盾预防化解中的作用。
通过乡规民约来化解纠纷,这是中国古代很多历史时期以及国外不少地方降低公共治理、司法审理成本,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的经验。而新时代的村规民约,除了吸收传统乡村共同体的治理经验,比如对常见的邻里矛盾的调处、传承良善文化、维护乡村治安外,还加入了实现基层民主、管理公共事务、分配保护财产、保护利用资源、维护环境卫生、推进移风易俗等目标。如书作者所指出的,村规民约往往能够比较好调解日常纠纷,这与国家法律的确认、社会环境的支持分不开,也与乡村固有的自治传统的发扬、村民集体认同心理的支撑有关。
但书作者也谈到,村规民约在化解纠纷方面也存在一些消极作用,甚至与法律规定相悖。实际上,一些基层地方的村规民约沿袭了封建、近代时期的一些传统做法,比如对违反村规民约的村民的处理,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又如有的村规民约并未经过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的广泛讨论,而主要由村干部商量决定。
这就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意义所在,也就是虽然与古代、近代一样都是在推行村规民约,但现有的村规民约应当确保与宪法、法律、政策的基本原则一致,基层政府尤其是法治部门应当做好对村规民约的过渡指导,并监督村规民约的合法性运行。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英姿在《完善司法确认程序,促成“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长效机制》一文中谈到,尽管近年来,我国多元解纷机制取得了长租发展,非诉讼解纷方式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已经卓有成效,在社会风险易发领域,非诉讼解纷渠道的制度化已经基本成型。但仍然有待于人民法院强化司法审查机制建设,使得非诉讼解纷方式能够比较好地纳入法治化处理的轨道,能够使得社会矛盾的处理遵循实体法逻辑,确保矛盾纠纷的解决不损害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利益,对于矛盾纠纷双方的利益处理不损害公平原则。
所评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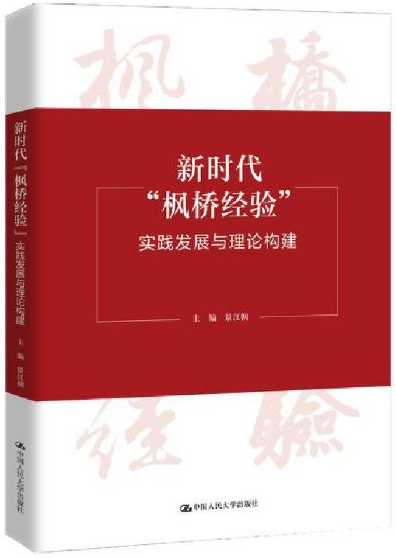
书名:《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发展与理论构建》
主编:景汉朝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8月
供稿人:陈 麟
初审:戴佳运
复审:陈 麟
终审:张维特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