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不必说了,不如现在就开始阅读吧。”
这是傅小平在随笔集《普鲁斯特的凝视》一书所作长篇序言里的末尾一句。什么都不必说了,阅读才是硬道理。说起来,我阅读也有几十年了,阅读的范围和内容除古典传统书籍和现代部分经典作品之外,阅读最多的就是外国文学。有一年,我读英国作家玛丽娜·柳微卡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一位朋友看过封面后啧啧称奇:“伙计,你怎么什么书都读?!”还有一次,一位本土女诗人在我谈到赫拉巴尔时,她一脸懵逼,问赫拉巴尔是谁?后来在她的随笔里见她大谈赫拉巴尔,那架势好像赫拉巴尔是她发掘出来似的,不免有些好笑。但这次阅读傅小平先生的两部随笔集《普鲁斯特的凝视》和可以视为姐妹篇的《去托尔斯泰的避难所》,我感到无比的羞愧。因为,打开《普鲁斯特的凝视》目录页面,我发现竟然有包括托马斯·基尼利、科尔森·怀特黑德、萨拉·沃特斯、基兰·德赛、安娜·卡瓦尔达、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瓦茨拉夫·哈维尔、塞斯·诺特博姆、安吉拉·卡特等在内的十二位小说家、诗人的名字,是我没有见过的,更遑论阅读了。因此,对我来说,这次阅读不仅有益于我者甚夥,更关键的是我找到了一位令我仰慕的同好者——傅小平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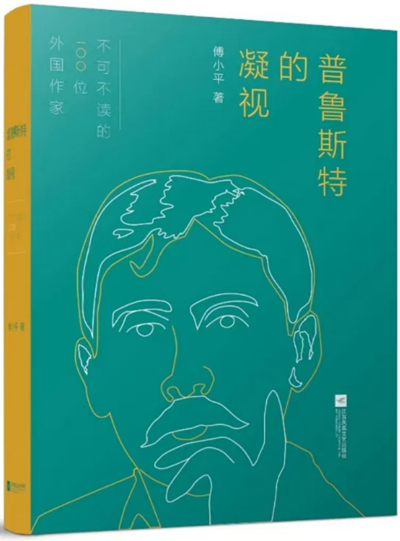
《普鲁斯特的凝视》
作者:傅小平
定价:80.00元
开本:32开
页数:725页(22.625印张)
ISBN:978-7-5594-2135-7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上市时间:2019年3月
傅小平说:“大体说来。我这些年写的文字里,更被作家学者看好的是对话访谈。而不管是专业读者还是普通读者,着实有一部分更偏好我写的这些外国作家。”我就是其中的普通读者之一。我特别喜欢“凝视”这两个字,想起十三年前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时的情景,查看当年的阅读笔记《我的文学地图》:“在低洼的小路上,我停下了脚步,童年时代温馨的回忆打动了我的心:从哪经过修剪、闪闪发光、探到路边的树叶上,我认出了一簇山楂树,可叹自暮春便落了花。”心想,普鲁斯特当年凝视过的花花草草、贡布雷的春天、还有奈瓦尔的《西尔薇亚》,我也通过他一一地凝视过。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提醒读者,真正的阅读是“我们必须踮起脚尖,用我们最警觉和清醒的时间去进行的阅读”。这也正是我阅读这两部随笔集的态度。
话说,傅小平曾主持文学报“环球”栏目达五六年的时间。由于当年《文学报》正处于艰难的转型期,再加上稿酬等问题,很难约到理想的稿子。但“环球“栏目还要办下去,与编辑部协商后,他决定用笔名自编自写。这一写就是若干年。傅小平首先追求的是“文字要好读”,这对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强调文章的新闻性,又必须与文学相匹配。这个栏目深深烙下傅小平本人的印记——有学养深度,但避免学术化;有客观理性的评述,但更须有自己的见解;选择合适的切入口,让普通读者迅速进入作家的文学世界,消解他们对作家作品的困顿与迷惘等等。为此,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文学突发事件,包括大作家新书的出版、有世界性影响的书籍颁奖活动等等,不错过任何可以让作家“曝光”的时机。因此,傅小平笔下的活脱文字,就成为独具傅氏风格的“刻绘”,完全不同于偏重于故事梗概的写法的那些味同嚼蜡的高头讲章。
对于傅小平来说,他不是为生活而写作,而是为读者而写作。他用温和的方式抵抗这个喧嚣的时代,微薄的稿酬没有消减他写作的热情,反而更刺激他要做出好文章。他无所谓禁忌,却留给了同行一个不屈服的背影。
《普鲁斯特的凝视》分为十辑,共一百位各具特色的外国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书里到处都是奇闻逸事,值得成为文学爱好者,尤其是外国文学的爱好者的枕边书。而《去托尔斯泰的避难所》在写作内容的辑选方面可谓是创新之书籍,它的副题是“影响中文书写的100位文学大家”。包括海外篇、渡海篇和海内篇,三个群体像“星链”一样实现无缝对接——外国作家和作品,经由中国一流的翻译家,抵达国内的作家。这是一条重要的连接通道,有没有这条通道,当代中国文学建构能否取得现在的成就,能否具有现在的样貌,很难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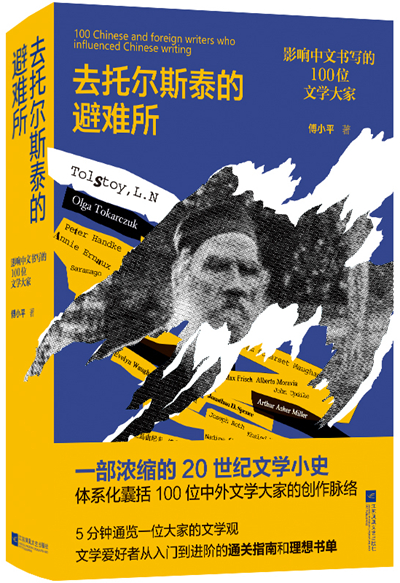
《去托尔斯泰的避难所:影响中文写作的100位文学大家》
作者:傅小平
ISBN:9787559469793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页数:720
定价:98.00元
这两部随笔集总厚度达1400多页,言之有物,可谓篇篇精彩,是近几年以来,书话笔记类散文书籍中之翘楚者,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书。笔者感到遗憾的是这两部随笔集宣传太少,致使诸多爱书人与之擦肩而过,甚为可惜。傅小平在《去托尔斯泰的避难所》的自序里说:“我想起乔治·斯坦纳的感叹,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马佐夫兄弟》,谁会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但倘是没有那些敏锐的敲打,又怎么体会我们得以奔赴的避难所的浩瀚与伟大,而敲打于我是力所不及的,我只是发出呼唤罢了。”两部随笔集的序言经过五年的沉淀,面目仿佛更轻松与愉快了一些,沉重是必须的,但轻松才是“诱引”阅读的不二法门。
傅小平在文章的题目上所花费的心思,尤其值得称道。譬如《西格弗里德·伦茨:永不谢幕的“德语课”》。伦茨是德国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就是《德语课》。前些年我还读到他的一本小书《我的小村如此多情》。因为职业的原因,傅小平能接触到、采访到国内一些一流作家,并在文章中直接加以引述他们的观点,这是第一手新鲜的资料,可读性就大大地增强了。这也是这两部随笔集的优势所在。阅读始知莫言和余华等作家对伦茨的仰望和崇敬。我绝对没有想到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亡军的将领》是贴着《德语课》的封面偷渡到西方的。卡达莱在今年7月1日病逝,他是我喜欢的作家,重庆出版社“重现经典”小精装出了他的《长城》《梦幻宫殿》《亡军的将领》《破碎的四月》,我皆有藏读。傅小平善于把一些他人不知道的趣事逸闻穿插其中,确乎是妙手文章,一招鲜。
再譬如《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一个人可以在一生任何时刻开始写作》。我读过她的几部小说,并且看过三遍由《书店》改编的同名电影(堪比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的《查令十字街84号》),一个小镇竟然在“黑恶”势利逼迫中容不下一个小小的书店,最终被大火吞噬——她生活十年的小镇并不需要一个书店,而放火的小女孩(即便烧毁,房子也不能落到“黑恶”势利之手)曾经是书店惟一的员工。因此,当我看到傅小平写了英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竟然感到格外的高兴。但我并不知道菲茨杰拉德六十岁才开始文学创作的,我只知道北京的止庵对菲茨杰拉德非常推崇。这一段话傅小平说得真是到位:
“可以确定的是,从佩内洛普提笔写作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她的与众不同。她不曾有强烈的功利心,意图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不曾怀有惊世骇俗的野心,想要写一部《追忆似水年华》那样的鸿篇巨著;也不曾有前辈或同时代本国女作家夏绿蒂·勃朗特、简·奥斯汀、艾略特或莱辛那样满怀自我和社会表达的渴望和诉求。或许,她最大的愿望,仅仅是经由回忆,记录下生活中那些细小琐碎的瞬间,聊以打发漫长的英国黄昏。”
果然被我猜中,傅小平在《阿尔贝·加缪:活着,在荒谬中反抗》里起笔就写到那场惨烈的车祸。那一天是一月四号,一九六〇年。萨特和波伏瓦也表示了沉痛的哀悼。据说,波伏瓦冒着寒冷的细雨在巴黎街头徘徊。我藏有《孤独与团结:阿尔贝·加缪影像集》,其中有一张照片在我过目第一眼的瞬间,眼泪唰地就流出来了,加缪的母亲的一帧侧影,她目光所及之处是加缪英姿飒爽的照片。加缪谈到曾说:“我们有爱,就算话说完了,也不是一片寂静。”
傅小平谈到加缪说:“正是贫穷和苦难的人生,形成了他的荒诞和反抗意识的萌芽,当然还有对爱和自由的执着追求。”我同意这个观点,诚如加缪所说:“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播撒着它的财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加缪和萨特一样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作家,这种影响仅限于写作技巧方面。就写作而言,西方作家扮演的社会批判性角色,要远远强于国内的作家。甚至于可以这样说,中国作家已经失去了作家对社会应有的批判性,只是一帮拿稿费、经营各自地盘的码字匠而已。
加缪死了,但勒·克莱齐奥还活着。我最早阅读克莱齐奥的小说,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诉讼笔录》。傅小平所写的题目是《勒·克莱齐奥:用温和的方式抵抗,并且“远离”这个世界》。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陆续出版了他的作品,我也买过,包括《燃烧的心》《奥尼恰》等,但始终没有再去阅读他的兴趣。倒是没有想到克莱齐奥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他喜欢鲁迅和巴金的小说,尤其喜欢老舍,“我发现老舍的小说中的深度、激情和幽默都是世界性的,超越国界的。”而且他在南京大学授课之余,他还专门到莫言的老家去看过。到底是西方作家的做派,自由而坦荡,克莱齐奥认为:尽管中国文学的创作力量不可低估,但目前在世界文学领域的影响力确实有限。傅小平在文章的最后指出这一点,不算是给中国文坛泼冷水吧。
二〇一九十月八日,在飞赴法兰克福,转往伊斯坦布尔的途中,我一直在阅读奥尔罕·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在此之前读过他的《我的名字叫红》、《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还有其它几部小说。我此行土耳其的目的就是冲着帕慕克来的。纯真博物馆的第一件藏品是芙颂落在凯末尔蓝色床单上的那只蝴蝶形状的耳坠,再过几天,那枚用芙颂耳坠的形状做成的印戳就会盖在我手里的这册书上(第五百四十八页的空白处,凡是中国游客到纯真博物馆参观,只要带着中文版《纯真博物馆》,可免门票费),成为一份独特的纪念。我很想知道傅小平是如何“刻绘“帕慕克的。文章的题目《奥尔罕·帕慕克:作家的真实性取决于他融入自己所在世界的能力》。帕慕克说:“作家的真实性取决于他融入自己所在世界的能力,取决于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变化的身份的理解能力。”既要融入世界,又要随着身份的变化而变化。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那次土耳其之行,因为时间的原因,谒访纯真博物馆未果,大为遗憾,乃至组织者来到笔者的房间深表歉意。我的书籍留给当地的导游米娜,她答应帮我实现这个愿望,果然在当年十一月十五日,米娜发来她前往纯真博物馆拍摄的照片,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在我带去的《纯真博物馆》里钤盖芙颂耳环印戳的照片,印泥是红色,耳环是镂空的蝴蝶状的,令我欣喜不已。
帕慕克说,作家无论国内国外,他们都在为理想的读者写作。笔者算是理想的读者吗?若是,那么,傅小平先生就是超级的理想读者。他是中国的哈罗德·布鲁姆——因为他作品强烈的文学性和引发浓厚的阅读兴趣的“煽动性”。
世界很大,好的作家和书籍很多。我们尤其需要像傅小平这样“深读浅出”的引航人,来激起普通读者的阅读一本纯粹的文学书籍的兴趣。
繁华落尽,记忆留痕……
(姚法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藏书家)
(供稿:许立昕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