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0年,吕后“驾崩”,刘氏宗亲连同勋贵诛杀诸吕。刘氏诸侯王中,所婚配的吕氏女及其诞下的刘姓子嗣也“不约而同”迎来暴毙。
勋贵并不希望迎立汉高祖刘邦的长房长孙齐王刘襄。刘邦庶长子刘肥诸子,在诛杀诸吕过程中立下大功,功勋卓著,而刘襄作为刘肥的长子,一旦即位,将必然导致勋贵在政治上被迅速陷入边缘化,诛杀诸吕的功劳也会被忽略不计。因而,勋贵以刘襄的舅舅凶横为由,认为刘襄不是合理人选。
如果场景换到明代,如果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也出现了类似的选储难题,勋贵集团也不会选择军功最高、年龄最长的燕王朱棣。
汉初勋贵选择了代王刘恒。刘恒在高祖和吕后时期,算得上是政治上的小透明,其母亲薄姬以及母族薄氏都十分低调,这被认为易于掌控。
刘恒被成功迎立后,通过安抚勋贵,安插亲信得以掌控局势,但很快就显露了自己的锋芒。诛杀诸吕的首功者周勃获任丞相,很快以列侯归国的名义免职,之后,文帝刘恒以周勃在家披挂战甲、接待客人时手拿兵器存在谋反嫌疑为由,将周勃下狱。周勃不得已托人找到薄太后,最终才得以释放。
文帝在位期间致力于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厉行节约,并改革汉朝继承的秦律中的严苛条文尤其是废除肉刑。他还致力于安抚南越,派人修复了真定的赵佗祖坟,并致信赵佗,最终推动南越撤掉帝号,获得事实上的自治地位,以汉朝分封的王国名义存在。
汉文帝为抵御匈奴带来的边境威胁,采用整体性防御政策,招募内地百姓充实边地,建立事实性的屯田,还在边地建立马苑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匹。这些为后来武帝时期汉朝大规模对匈奴用兵打下了基础。
文帝在历史上广受赞誉,被认为是圣明之君,但对待周勃等非代国系的功臣的态度上,就不失刻薄。新出版的《史说汉文帝》一书指出,文帝刘恒对于代国“从龙”旧臣的态度,就非常宽仁,甚至几近纵容。比如对于张武受贿,不仅没有严厉处罚,而且还拿出皇家府库的钱财给他,说是要让张武羞愧感悟。
文帝的舅舅薄昭被封车骑将军,在其封地,薄昭之侄薄贵仗势欺人。文帝派出朝臣钟毓前去处置,处斩了薄贵。得知此事,薄昭将钟毓掳回府中予以虐杀。在这种情况下,文帝亲自祭奠钟毓,迫使薄昭自杀。文帝还宠幸纵容诸如邓通等人。对于文帝纵容亲贵、亲信的作风,历代史官也持批评态度。
刘恒对于异母弟、淮南王刘长也采取了纵容态度。刘长多次违反法令,甚至因私忿打死辟阳侯审食其,对此文帝也没有追究。刘长因而更加骄纵,频频违法犯禁,以至于走上谋反道路。刘长因而被处罚剥夺王号,流放过程中绝食而死。对此,文帝十分悲痛,下令杀了押送囚车的吏卒,还将刘长的四个儿子先后封侯、封王。当然,也有史官认为,文帝此举采取的是类似于“郑庄克段于鄢”的捧杀策略。
《史说汉文帝》书中在谈到汉景帝刘启时指出,景帝秉承父亲俭朴之风,但“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景帝刘启在做太子时,就曾失手致死吴太子,这是七国之乱的重要起因。移动互联时代,“鬼畜”创作up主纷纷将刘启称之为“大汉棋圣”,与大明战神朱祁镇并列。
景帝不喜太子刘荣,将之贬为临江王,又因捕风捉影之事将刘荣交由中尉府处置,“任由(中尉)郅都横加责讯而不予过问,以至于刘荣连给父亲上书谢过的机会都没有,最终导致一个颇受民众爱戴的藩王枉死”。对待自己的儿子如此凉薄和冷血的帝王倒是不少,但很少出现在以宽仁著称的帝王身上,景帝刘启创造了这样一个难堪的记录。
景帝刘启刻薄寡恩的另一个实据,就是对待晁错。晁错推动削藩,而景帝予以采纳,引发七国之乱,这只是表面现象。从汉高祖兼用分封制和郡县制,到文帝纵容诸侯,其间还有文帝刘恒上位时勋贵罔顾刘氏宗亲诛杀诸吕贡献、刘启自己误杀吴王太子的往事,七国之乱本就是不可避免会发生的结果,并不能一概解读为晁错献策失当。以景帝的政治智慧,不难看出吴王反叛的真实原因,却一厢情愿地以为杀死晁错可以暂时平息诸侯作乱,而且对于晁错的诛杀非常暴烈残酷,不由分说。所以,当举起反旗的吴王听闻景帝杀死晁错的消息后,也不禁予以嘲笑。
在对待平息七国之乱的最大功臣周亚夫问题上,景帝采取了折辱臣下尊严的态度,导致周亚夫在诏狱府中被反复揶揄侵迫,最终绝食五天,呕血而死。两汉末年,均发生了权臣侵辱弱帝之事,社稷因而倾覆,但这何尝不是景帝辱臣的因果呈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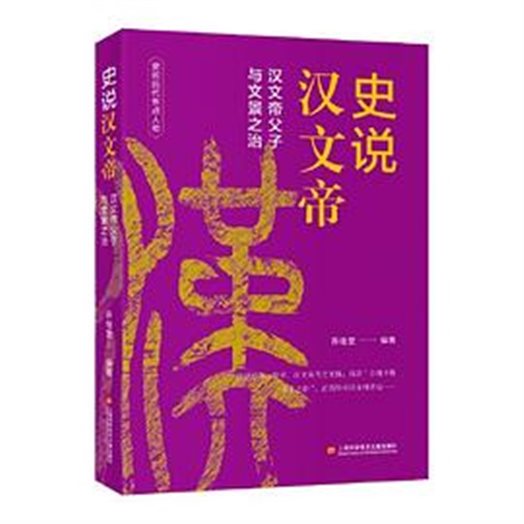
书名:《史说汉文帝》
编著:乔继堂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3月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