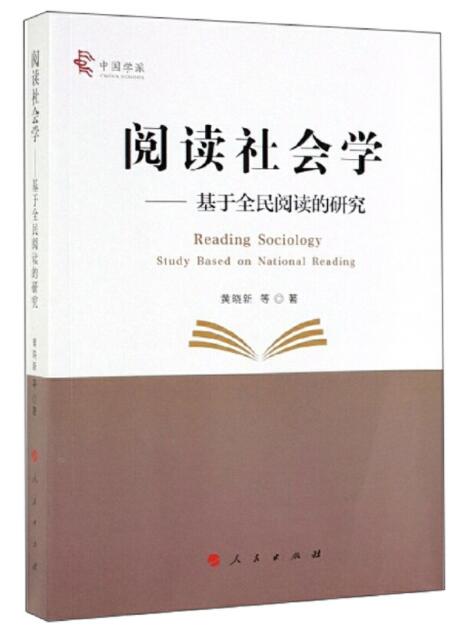
除首章概述了“阅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之外,从第2章开始,依次叙述了阅读的社会过程及效能,阅读及阅读接受的社会心理,阅读的社会结构及人际互动,阅读的社会产业,阅读的社会组织,阅读的社会保障,阅读的社会控制,阅读的社会调查、监测与评估等议题,呈示了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全民阅读问题的学科内涵,为中国内地进一步深化、拓展和创新全民阅读工作,提供了新的学理滋养。
2018年8月1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先生在该书序言《阅读是个大学问》里,颇有激情地指出:“我为有人从社会学等学术角度研究、总结全民阅读而惊喜,因为读书在古今中外都是大学问。我也为本书内容精到而心动,因为读书本来就是人类精神发育的大事,是任何个体生命和不同群落社会化的必经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全民阅读是一个理论研究的创新”,全民阅读“要在高水平上突破,就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只有理论的前瞻性、预测性与权威性,才能真正动员和调动全社会力量,形成群众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衡量全民阅读社会实践的标尺,就是智力健全的公民,人人自觉投身阅读之中,并把阅读当成自己生活、工作乃至生命的一部分。”
作为一部填补现代阅读学研究空白的学术著述,《阅读社会学——基于全民阅读的研究》的作者,分别从政治学、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及图书馆学等学科视角,聚焦全民阅读,获得了诸多新的见解,并初步形成了“阅读社会学”的学科架构。
作者认为,阅读的社会结构,包含着作者、语言文字、文本、读者、出版者、传播者、阅读的时间与空间、阅读推广组织、阅读的活动氛围等基本要素,正是这些基本要素之间的排列与组合,形成了阅读系统的内在结构,而这正是全民阅读研究的重要基础。多年来,阅读的传统结构因信息和知识载体的革新而转型,以读者为本和阅读接受为中心的新阅读结构正在形成,全民阅读工作者须得关注并正视这一阅读学新潮,才能在与时俱进之中顺势而为。为此,作者们认识到阅读活动主体与客体,都是人类社会化的结果,因而挖掘阅读社会属性,掌握阅读的社会运行机制,是研究和推广全民阅读所必需的理论基础。
从宏观层面上来说,要把全民阅读工作做实做好做到位,必须要关注阅读的社会动力机制、阅读的社会保障机制等问题,因此,本书作者引入了“社会控制”及“社会保障机制”等社会学理念,来观照全民阅读所必须具有的理想社会架构。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应该借助中央和地方立法促进及行政规定、公共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力量,以作用于优良书、刊、报及数字化读物的生产出品、发行流通和阅读推广。阅读的“社会保障机制”,是保障大众阅读的基本条件。通过社会力量,帮助社会成员提高阅读情意,获取阅读能力,培养阅读习惯,满足他们对阅读的多元化需求,引领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总之,通过对全民阅读活动做适当的“社会控制”和必要的“社会保障”,才能促进社会大众阅读的正常开展和不断发展,是实现全民阅读可持续良性发展的有效手段,也是阅读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内涵。
因此,柳斌杰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总结《阅读社会学——基于全民阅读的研究》一书的四个特点是,首次超越了以往习见的对个体阅读的具象研究,开辟了以社会视角从事全民阅读的新路径;以人为本地创新了阅读学的理论,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阅读社会学课题;从问题导向出发,提出了比较严密科学的阅读社会学研究逻辑体系和总体框架;知行合一地对全民阅读的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对全民阅读活动具有实践指导的重要作用。
正如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尔皮在1958年初版的《文学社会学》中所指出的:“一切文学现象……都是以创作者、作品和读者大众为前提的”,阅读现象自然也是以著作者、读物和读者大众为前提的。而全民阅读理念的提出,正是要以人为本,最大程度地引导大众从“潜在读者”向“现实读者”的身份转化。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作者指出,只有当社会个体的阅读行为拥有适度动力的时候,才能保持全民阅读可持续良性发展的有益态势。为此,还应从读者的社会心理层面去研究阅读动力机制问题,阐释阅读动力产生的内部机理和外部环境因素。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全民阅读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最应该从千家万户与万户千家的学习型家庭做起。古今中外的读书史充分证明,一个孩子的语言、文字启蒙越早,接触图文并茂的启蒙读物越早,越有利于建立孩子的读书情意和阅读兴趣,培养终身阅读习惯,促进其心智的健康发育与健美成长。
在这方面,非常值得中国内地全民阅读工作复制的,是英国政府开展多年的“阅读起跑线计划”(Bookstart)。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为学龄前儿童提供阅读指导的全球性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为每一个婴幼儿免费提供一个“阅读礼包”,内容包括根据孩子不同年龄段阅读特点研发的读物、分级的推荐书目、父母导读手册,乃至健康保健资料及涂鸦笔、各色蜡笔、各种书签等。发放“阅读礼包”的目的,是为了让婴幼儿从出生起就能接触书本读物,加强学前教育,提升儿童阅读素质,增进“亲子共读”,保障贫困地区孩子的阅读权益等。“阅读起跑线计划”传播到中国内地以后,被苏州图书馆率先接受,并在实践中逐步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话说该书序言作者柳斌杰先生,在担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及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是一位热心发动并积极推动全民阅读进程的专业行政长官。他在上世纪四零年代末出生于陕西长武,正是在母训教诲之下,成为一个拥有终身学习习惯的读书人的。他回忆说:“我是一个忠实的读者,很早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原因是母亲临终前叮嘱的一席话,让我受用了一辈子。她说:‘我没有任何财产留给你,但一句话要你记住:读书是正道,知识是你的,水冲不走,火烧不了,能帮你。’从此,再穷也要借书读,再苦也要去上学。上学时正值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图书馆很多书不让借,每个假期我都自愿去整理校图书馆,钻在里面看书。在‘文革’那种图书贫乏的时代,我就只能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1978年我到北京上研究生,在大学校园那时候买本好书还要早上4点钟去排队,特别四开始引进和翻译进来的外国学术名著很抢手。”
无独有偶。上世纪六零年代初出生于湖北洪湖的黄晓新先生,在本书后记中也忆及了自己的童年读书生活。令人在开卷阅读之余,不由得不掩卷沉思。黄先生说:“我从小就喜爱书籍和阅读,至今还最爱逛书店和图书馆,一扎进去很久,沉湎于乱翻书不愿出来。记得在农村读小学时,有次我随大人到离家最近的镇子,第一次见到一家小图书馆很是兴奋。说是图书馆,其实只是一个小的阅览室……我废寝忘食地在里面翻看了一整天,小小少年对外界的好奇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心想,世界上还有这等好事,不要钱,还能安安静静读各种书,以后可常去,这应该是比天堂更美妙的生活”,但被“文革”波及后,少年的“阅读梦”随之破灭,“在那个出版和文化荒芜的年代……我只能从地上和垃圾堆的废纸篓里捡些散页和纸片来读”,直至国家恢复“高考”,于1979年秋入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论者以为,一个孩子只有在“学习型家庭”中不失时机地获得阅读启蒙,才能成为“书香校园”的参与者,并进一步拥有“终身学习”的人文情意。惟其如此,一个“书香中国”的美好文教愿景,才有望逐步转化成为真实的社会场景。而这,正是《阅读社会学——基于全民阅读的研究》一书之终极关怀所向和根本价值所在。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