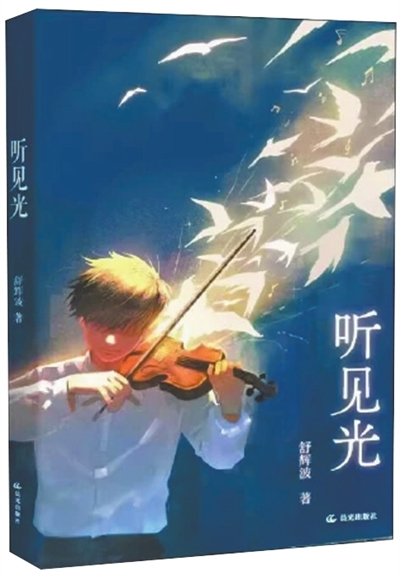
《听见光》
舒辉波著
晨光出版社2025年4月版
45.00元
ISBN:9787571522186
舒辉波的非虚构儿童文学力作《听见光》以强烈的在场感,深度呈现当代中国良善、包容、向上的社会场景,引发读者对个体与他人、社会和时代关系的深入思考。这部记录青年盲人小提琴演奏家张哲源成长轨迹的作品,有意识地采用听觉、触觉等去视觉化叙事,并通过“对话体”写作,以“平等话语”重塑了弱势群体的书写范式,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拓展了全新的精神领域,其独特的探索精神和艺术价值,达到了非虚构儿童文学的新高度。
从“俯视同情”到“平视对话”:理解与爱始于平等和尊重。
《听见光》是中国儿童文学在弱势群体书写上的重要突破。长期以来,弱势儿童——尤其是残障儿童——往往被贴上“需要帮助”“值得同情”的标签,弱势儿童在文学中的形象往往被简化为“励志符号”或“苦难象征”,却很少被真正理解。关爱,不是俯视地同情,而是平等地倾听。《听见光》的突破性意义在于,舒辉波并未将张哲源塑造成一个被动的“受助者”,而是以真诚的平等和尊重,展现了张哲源作为普通孩子的喜怒哀乐,以及他在音乐中寻找自我价值的完整历程,将主人公塑造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主体。他并未放大张哲源的孤独与苦难,而是将其成长中的困难、挫折与爱、希望、梦想融为一体,呈现了一个真实可信又充满魅力的形象。
《听见光》每一章设置的作家舒辉波和主人公张哲源之间的访谈实录,呈现独特的非虚构写作文体特征。这些对话部分预叙了本章内容,形成了叙事悬念与张力,更体现出非虚构写作的“在场感”,将作家对于生命、艺术的思考和张哲源本人的思考、困惑与梦想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叙事方式,让弱势儿童成为自己生命的主角,拥有自己的声音。正如哲源所说:“尊重他们,并且相信他们的能力,平等待之。”这句话不仅道出了盲童的心声,更是对全社会的一次提醒——真正的关爱是平等的对话与信任。
尤其令人动容的是,作品展现了生命在极限挑战中迸发的韧性。视障本是所有残障中最困难的,而张哲源选择的偏偏是弦乐器中最难驾驭的小提琴——没有视觉反馈,只能靠听觉和触觉调整音准;无法观察指法,只能靠手指记忆琴弦间距;无法模仿姿势,只能通过老师手把手调整形成肌肉记忆。这种“双重困境”下的突围,将奋斗置于近乎不可能完成的境地。
张哲源的故事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理:弱势儿童需要的绝非降低标准的“特殊照顾”,而是平等的发展机会与真正的信任。当社会提供足够的支持,生理的局限终将被精神的力量所超越。这正好呼应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的崇高理念:“把最好的书给最需要的孩子”,而《听见光》更进一步——它不仅为视障儿童提供了精神共鸣,更让健全读者学会如何真正理解、尊重和关爱那些“不一样”的生命。从而以哲源为镜,反观自我,从哲源身上的局限和困境,看到每个人自身的局限和困境,这使得《听见光》的书写呈现出“从个别的事物走向本质的共通,具体的形象趋于抽象的普遍”的特点。
“去视觉化”叙事,以真实铸就榜样的力量。
《听见光》最引人注目的艺术突破,在于其开创性的“去视觉化”叙事。作家通过细腻的听觉、触觉、嗅觉与心理感受描写,构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健全人认知的感知世界。张哲源寻找爷爷时依靠对路灯杆的触感、对草木清香的嗅觉、对戴胜鸟的鸣唱来定位方向;在芝麻秆地里通过蜜蜂的嗡鸣、蚂蚱展翅的“沙啦”声与植物的湿润触感与自然对话。这些描写正是对盲人生存境遇的真实还原与艺术再现,让人物形象有了坚不可摧的根基,也让读者对人物感同身受。
这种叙事尝试的突破性在于:它既是对特殊群体生活的真实还原,也是对健全读者感知能力的唤醒。当作家舍弃视觉描写,转而用声音、气味和触感叙事时,文字便产生了“让熟悉变得陌生”的艺术效果——读者被迫脱离习以为常的视觉依赖,进入一个更为原始而鲜活的感知领域。正如书中所说:“他的耳朵和手上都长着眼睛”,这句话生动诠释了感官代偿的奇迹。
作品中“听觉叙事”的运用尤为精妙。那些超现实的听觉体验——能“听见露水从星星上落下的声音”,从燕子妈妈呢喃声的变化中得知小燕子的破壳,在已关闭的音乐餐吧前幻听到的往日乐声——既展现了主人公独特的艺术感知,也为读者打开了想象力的闸门。通过这种多感官的叙事手法,《听见光》实现了非虚构写作中罕见的诗意真实。
真实性、文学性、儿童性的叠加,完成非虚构儿童文学的三重超越。
非虚构儿童文学向来面临三重挑战:真实的严谨、文学的温度、儿童的可接受性。《听见光》的成功之处,在于舒辉波以深厚的文学功力完成了这三者的完美叠加。
曾担任电视台编导10余年的经历,赋予舒辉波纪录片一般的叙事天赋——像镜头般精准捕捉细节,又如显微镜般深入心灵。其文字不急不躁,细腻入微,让笔尖探入人物的心里面。书中,哲源的听觉世界被描绘得充满诗意:眼泪滴落琴弦的“轻微声响”,水库边大鱼跃动的“哗啦声”,姑妈声音里“棉花糖般的甜”。这些通感式的描写,让看不见的黑暗化为可触可感的艺术之境。
在儿童接受性问题上,《听见光》采用了“问题式对话”的叙事方式。每章开篇的访谈设计直击儿童心理:“你的梦是以画面还是声音呈现的?”“说说你的一年级”简短的问题如一把钥匙,瞬间开启小读者的好奇心与共鸣之门。这种牵着孩子的手走进故事的方式,让沉重的生命主题变得可亲可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舒辉波的文字始终保持着“不急不躁”的节奏,以朴素克制的笔法聚焦情感的褶皱。在描写哲源与姑妈离别时,作家仅用“姑妈拉过他的手,让他握住一根细细的竹签,说,‘来,尝一尝棉花糖是什么滋味’”——寥寥数笔,无尽的眷恋与生命的韧性已力透纸背。这种留白艺术,让沉重主题获得了轻盈的表达,体现了非虚构文学的艺术新高度。
《听见光》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深邃的隐喻。它告诉我们:光不仅存在于视觉中,更在平等相待的目光里,在打破偏见的行动中。这部作品既为残障儿童提供了“被看见”的窗口,也让健全孩子学会以尊重之心看待差异;既是一部个人奋斗史,更是一面映照社会文明的镜子。
舒辉波用非虚构的笔、文学的深厚功力与作家的责任,为中国非虚构儿童文学树立了新的艺术标杆。这部作品值得被铭刻在经典序列中,因为它不仅让我们听见黑暗中的光,更教会我们:每个孩子都是值得被世界听见的光源。
(供稿:王茜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