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嫁需钱财,《礼记·昏礼疏》说,“纳征者,纳聘财也”。男家聘礼的厚薄,女方妆奁的丰约,成为两家考虑的因素,这就使得富家人家往往只考虑与同等身家的人家缔姻,而平民百姓则无法高攀。
明朝中叶以后,婚嫁的排场已经变得非常夸张。一些出身贫寒,骤得富贵的家庭,结姻高门,必然要讲排场。尤其是江南沿海地区,婚嫁排场尤其惊人,不仅真正意义上的富豪要斥巨资经办子女婚嫁大事,而且小康家庭哪怕借贷也要充场面。
到了清代,尤其是中期以后,这种风气已经变本加厉,“富家嫁女务侈妆奁之丰厚,贫家许字尤索重金,甚有因嫁女而荡产,缘娶妇而倾家者,以至穷苦小民,老死而不能婚”。这种风气席卷到了国内许多地区。比如湖南桂阳县,乾隆以后,女家以奢华为时尚,衣服由棉布改绫缎,首饰变铜角为金银、珠翠,水涨船高,男家的聘礼也一增再增,哪怕是中产之家,也难以担负。广东博罗县,乾隆时候起,人们结亲,从论门第变成直接讲钱财。河南内乡县,康熙以后,婚姻就多论财,女方父母苛索聘礼,男方也要计较妆奁厚薄。就连大西北的陕西洛川县,雍正、乾隆之际,也掀起了婚礼讲排场的风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郭松义所著的《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一书。这本书借助史料计算了清代中后期各地婚聘财礼负担。雍正初年,各省聘礼在40两-300两不等,而到了嘉庆年间,山西长子县,“巨室百金,庶民钱数千”,山西乡宁县在光绪末年,聘金为“200千”。雍正年间,浙江当地,“嫁女费银数百两至数千两”,到了清末,浙江黄岩县,则需数千金。同样,在广东广州等地,乾隆、嘉庆之际,“嫁一女,娶一妇,用银至数百两、数千两之多”;广东阳江县,道光年间“动逾千金”。在福建不同地区,婚嫁耗费行情不同,但哪怕最低,也要“百余金”。
也就意味着,无论南方北方,不管沿海还是内地,一次婚嫁耗费少则几十两,多则百余两、几百两,甚至上千两,对于各地中产之家都是非常沉重的。“一娶一嫁,使本不富裕的家庭几乎陷入窘境”。浙江温州一带,更有嫁女“破娘家”的说法。
《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书中指出,婚嫁花费奢靡之风,冲击了传统礼制。尤其是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婚嫁排场越来越大,这不免触犯朝廷规定,口子一开,将无法抑制。比如婚嫁宴请用笙鼓细乐助兴,新人花轿之前要鸣金开道,依照礼制需要贵胄品官才能为之,但各地白丁之家不惜斥重金为之,这当然就是僭越。
虽然清朝朝廷和地方官府对于礼法僭越现象十分警惕,动辄开展整治,还以反对浪费为名对百姓进行劝导,但如书作者所说,商品经济发达本身带动了阶层流动,很多骤得富贵的家庭希望通过排场豪华来弥补与高门的家世差距,这种做法很容易通过财富运作而得到事实上的豁免,更因此上行下效,最终无法杜绝。
婚嫁奢靡对于传统婚姻秩序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不同于近年来兴起的男方向女方单方面交托彩礼的做法,明清时期的婚嫁耗费,男女双方家庭都要花费巨资,总体上是相当的,如果男方付出高额聘金,而女方给出的陪嫁十分可怜,女方在新家的地位将得不到保证。而女方家庭更是会受到讥讽,所以为了给嫁出去的女儿以颜面,给女方家庭以脸面,就必须尽可能丰厚配给妆奁。
很自然,一个社会中权势、财富的分配总是高度不均衡的,多数百姓的家庭财力有限,婚嫁奢靡、攀比之风下,难以摆脱,这种情况下,很多适龄男女将得不到婚嫁的机会,更有甚者,家贫者不惜溺婴。尤其是贫民家庭惯以溺杀女婴。
这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虽然总体上适龄男子不能不娶,女子不能不嫁,但是实在无法嫁娶,光棍男子在家庭中仍算得上是劳力补充,而女子在农业社会的家庭中只能承担辅助性、补充性角色。
《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书中检视多地地方志发现,明清不同时期各地均有大量溺杀女婴的记录,尤其是在嫁娶奢侈之风兴起后,溺杀之风便陡然升温。这也是清代民间始终有忌讳生女、养女看法,将女儿看成是“赔钱货”的说法。这种情况下,各地的男女性别比例便严重失衡,从而使得家贫男子更难成婚。
总的来说,《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这本书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清代婚姻以及相关联的社会关系,采用伦理学、心理学、统计学的研究理论,汇集了方志、族谱、年谱、档案等历史文献,对清代的婚姻关系作了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全面研究与考察。书中内容涉及清代婚姻的社会圈、地域圈、婚育年龄、童养媳、入赘婚、妾、节烈妇女和贞女、妇女再嫁等问题,考证坚实,富有创见,对于读者了解清代社会尤其是家庭、婚姻问题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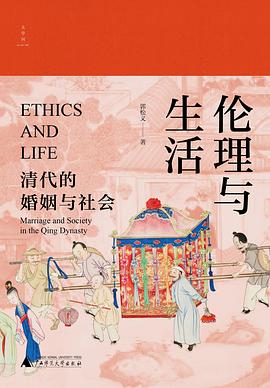
书名:《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
作者:郭松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5月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