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之铁:汉代铁工业与辐辏网络》以铁为钥,解锁汉帝国统治的隐秘脉络。聚焦关中核心区,作者林永昌教授通过考古遗存、简牍文书与跨文明对比,重构汉代冶铁工业如何以技术革新与官营垄断,编织出一张贯通都城与边疆的“辐辏网络”。从铁器标准化生产到工匠群体的生存依附,从跨区域物流到市场整合,本书揭示铁工业不仅是经济命脉,更是权力渗透、社会重组的关键推手。从长安陵邑的小型作坊到跨区域资源调配,铁工业的每一步转型都映射着汉王朝的统治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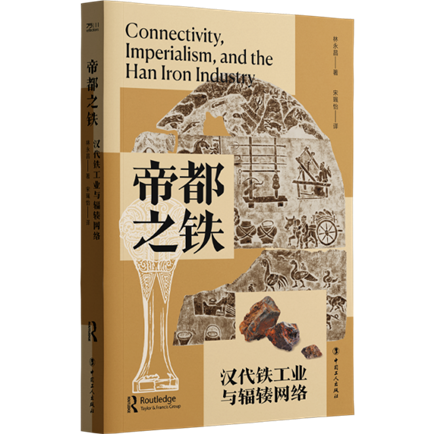
《帝都之铁:汉代铁工业与辐辏网络》林永昌著 宋珮怡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5年7月版/68.00元
样章:
绪论
国家制度与辐辏网络
历史学家劳榦先生(1907—2003)利用简牍资料,撰写过一篇综述汉代社会生活的短文。在文中,劳榦先生以传神的笔触描绘了西北边塞车马喧嚣的壮观场景:
在这条通往居延的大道上,车马、牛羊川流不息。这些车马,有的是属于朝廷的,有的是属于私人的。属于朝廷的有传车、传马以及从内地运送物资而来的车辆,而私人的车辆必须带有通关的符信。至于车的种类,有轺车(人乘坐的车)、方厢车(运输车)、牛车(盖有席篷的运输车)、輂车(驾马的货运大车)等。从内地运来的物资,主要有布、帛以及衣物。从附近的郡县运来的粮食(如果附近地区供应不足,也会从内地运来),包括谷(汉代,谷通常是指粟类,而不是稻类)、黍、麦、糜、穬等。这些物资都要被运到居延城里的仓库或障(秦汉边塞上险要处作防御用的城堡)内的仓库以及专用仓库。
这幅沉睡了 2000 多年的历史图景,幸赖居延汉简的考古发现得以重见天日。作为汉王朝设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军事要塞,居延肩负着抵御盘踞在欧亚草原的劲敌——匈奴——的重要使命。终汉之世,匈奴之患始终如芒在背。由于居延距都城长安远逾 1500 里,仅军械、粮秣、布帛及铁器等戍边物资的输送,便需耗时两月有余。若从关中以东的郡县起运,则煞费周章。
如今,居延连同其周边星罗棋布的烽燧障塞,早已湮没在浩瀚沙海之中。但在当年,在这条绵亘千里的补给线上,时有村落点缀其间,供往来商旅歇脚,获得补给。汉人深知,如此长途陆运不仅靡费甚巨,而且耗费时日。河西走廊既是维系都城与西域联系的命脉,又是预警匈奴来犯的咽喉。为确保这一通道畅通无阻,朝廷不得不倾举国之力维持这套边塞体系。纵使民生维艰,亦须竭尽全力将物资输往边关要塞。汉代横亘万里的防御链条,自东北发端,穿大漠,越流沙,终与敦煌及西域诸城遥相呼应。
承袭秦制基业,西汉王朝(含新莽时期,公元前 206—公元 25 年)完善了交通系统,通过构筑以都城为中心的驰道网络,将统治触角延伸至四境边陲。依托官方驿传和运输系统,朝廷政令能以日行 70 里的速度疾驰边塞,羽檄交驰之际,政令朝发夕至。这套精密运转的交通体系,成为维系辽阔疆域的根本保障。除却传递行政文书,汉王朝还在交通道路沿线广设仓储设施,用以周转自关东生产区输往都城及其以西疆域的粮秣、兵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朝廷为此倾举国之力征调徒卒。据以往简牍研究成果,居延戍卒多征发自今河南至东部地区,凡丁壮者皆须履戍边之责一载。因此,人员与物资的定向流动,实为汉王朝巩固政权的重要国策。
在汉王朝疆域内,交通网络的不断延伸与郡县制度的不断普及,不仅促进了信息与思想的交融,而且推动了不同生产中心所出物产的跨区域流通。得益于近年出土的大量有关西北边陲与南方县治中心的简牍,特别是官府文书档案,学者得以抽丝剥茧,还原汉代行政体系的运作机理。如今,我们既能洞悉郡县官吏的职司分工,亦能窥见基层行政单位(里)的运作方式。我们不仅清楚地掌握了中央政令的颁布流程,而且了解了县级官府如何呈报户籍、税赋,以及请示疑难案件的操作细节。
针对此类出土文书进行的分析,为理解政治整合提供了关键依据,并且从物质文化角度观察“大一统”的特征,如边城要塞普遍使用的汉式瓦当,更能揭示汉王朝统治面临的各种挑战。这些挑战既包括山川阻隔造成的地理障碍,又包括各方势力面对汉室时表现出的抗拒或顺应的复杂反应。鉴于汉王朝的整个疆域横跨不同的生态、地理和文化区域,出现这些挑战实在不足为奇。由于汉王朝统筹调配四方资源不均,以及各地供需的变化,朝廷不得不在幅员万里的疆域内采取“因地制宜”的治理方略。然则,朝廷究竟如何运筹帷幄,制定并调适政策,才能有效地治理地方?现存的出土汉代文献的地域分布恰呈跛足之势,也令解释变得窒碍难行。目前的出土材料主要集中于西北边塞(多属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与南缘临湘(属两汉时期;临湘,即今长沙)等地。纵使断简残编浩繁,然而关于货源地、运输路线、成本或其他市场交易的记录却支离破碎,
难以拼凑出不同地方之间货物跨区域流通的完整图景。加之,交通和通信系统本为官控而非商营,汉代文献很少会详载行程距离及运费,致使针对汉代货物运输进行的量化研究,犹似缘木求鱼。要之,若仅凭出土文书探究汉代制度及其社会影响,恐有管窥蠡测之虞。
为探究汉代版图扩大之实况,除了稽考传世文献,学者也对广布四方、风格趋同的汉式文物深感兴趣。汉代器物,如以黑、红为主色的漆器、带有流畅曲线的连弧纹铜镜、环首刀等典型器物,在边陲要地屡见不鲜。这为汉代实行“大一统”政策提供了佐证。这些考古学证据不独普遍见于汉域内郡,更在远至今越南北部、河西走廊、朝鲜半岛等地有所发现。这表明这些地域在汉代版图中与内郡高度融合。与此同时,标准化的随葬用陶器,包括鼎、壶、井、仓及灶之属,在汉代整个疆域内的中小型墓葬中俯拾皆是。由此可见,风格相同的文物在汉土的传播,意味着在文化领域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体化,亦代表着汉王朝将礼制从中原地区向外传播,其推行力度不亚
于施行大规模徙民实边的国策。
汉式文物流布之广固然毋庸置疑,但是最近有学者认为,当以更精微的视角审视此类“同质化”现象,重新思考其背后日趋紧密的辐辏网络(connectivity)a这一机制之所以重要,因其最终导致的“过程和结果甚至堪比现代全球化”。可惜的是,目前探究其实际运作机理的研究寥若晨星。从国家版图扩大的角度来看,汉王朝的考古资料尚未被充分挖掘,致使我们对汉朝体制的认识仍存空白。学界对汉王朝实行的“汉化”策略已有初步认识,但这种均一化的汉代社会的具体形成机制有待进一步剖析。考古学本可于此大有作为,在这一过程中提供帮助,无奈,目前出土的汉代材料的情况也是不尽相同。王侯宫阙、衙署遗址乃至日用器皿、农耕器具尚可觅得踪迹,而百姓的栖身之所多已荡然无存,致使市井生活难以一窥究竟。因这一局限,所以单凭考古发现实难尽释上述问题,尚需另辟蹊径以补苴罅漏。
比较研究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其中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对比研究为学界所重,而这种比较确有可取之处。以罗马帝国为例,其领土扩张和社会转型(所谓的“罗马化”过程),通常都是通过战争和大规模移民实现的,最终促成了思想观念和物质文化[如钱币和赭色陶器(terra sigillata)]的广泛传播。这种现象一般被称为罗马文明的“全球化”。此外,市场体系的整合使得商品能够被合理定价,这也成为罗马辐辏网络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虽然远距离贸易在人类历史上古已有之,但能够在广阔疆域内建立完整的交通系统,往往需要借助强大的国家之力来推动。其中,运输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刺激了商贸繁盛,而且优化了资源配置,与国家扩张形成了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从普通民众生活的角度来看,交通与通信设施的改进,将生产者、供应商与消费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形成地域性分工。
恰如布莱达· 迪林(Bleda Düring)对亚述帝国体制研究的最新洞见,所谓帝国,实际上指的是多种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以不同的程度成功地克服了地理阻隔与地方抗阻”。尤其当国家幅员辽阔、统治多个族群时,协作方式更显纷繁复杂。事实上,各行政区之间的联系模式往差异悬殊。 内维 里· 莫利(Neville Morley)也曾精辟地指出,纵使建立了统一的市场体系,罗马人亦无法如当代“全球化”那般“压缩”时空,因此难以建立一个完美的商品、原材料和信息流通网络。另有学者对“市场整合必循同一路径” 的单一假设提出疑问,罗马史家彼得·邦(Peter Bang)通过考察贸易网络,揭示了罗马帝国从未真正地整合地中海沿岸多样化的市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各类地区从广阔的贸易网络中受益的程度并不相同:作为交通枢纽的地区自然能够获得“全球网络”的优势,大片腹地及偏远地区则往往被忽视,发展相对滞后,沦为发展洼地。
要深入解析汉王朝版图扩大与巩固的内在机制,笔者主张聚焦辐辏网络这一关键的考古现象,并进行详细的研究。借助于当代以网络为基础的考古学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系统地阐释这一概念。具体而言,辐辏网络指的是遗址周边广大区域的交流互动,以及由政治和经济系统所驱动的各统治区的连接。这一复杂的现象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市场体系整合、网络扩张、技术革新、产业转型、信仰传播,以及旨在巩固国家体系的行政渗透等。
相较于仅仅识别遗址之间的地理关系,考古研究应重点考察辐辏网络的结构演变,这将有助于揭示社会交流的历时性特征变化。这一视角的转变,让我们得以通过古代统治者精心构建的国家统一现象,把古代帝国重新解读为一个由政治和社会交织而成的网络,从而进一步挖掘传世文献的弦外之音。因此,笔者认为,辐辏网络为研究提供了富有潜力的分析框架。要充分发挥其理论价值,需要着重考察商品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全链条,同时必须警惕对国家版图扩大进程的单一、简单化解读。反之,辐辏网络应该被视为一个重塑和改变社会关系与传统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同时受到了限制:每个政区都存在原有的社会结构,其中的旧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会与新发展持续角力。正是在这种碰撞、交融中,国家构建的辐辏网络得以显现,并在不同层面影响着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
尽管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比较研究颇具启发,但必须注意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汉王朝从未奉行真正的扩张主义,也并未追求所谓的“无限帝国”(imprerium sinefi ne)理念。汉武帝时期(公元前 141—前 87 年),朝廷通过实施郡县制,使得疆域拓展达到顶峰,但其施政重心始终在于巩固边疆——修建道路、调配国内资源,而非无限的军事扩张。这种强化交通基础设施的策略虽为古代国家所共有,但实施效果却因地而异,并且取决于当地的政治基础与社会传统。值得庆幸的是,就汉王朝而言,近几十年来积累了丰富的考古发现,配合其他出土文献,这些珍贵的材料能提供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信息,继而帮助我们窥探辐辏网络实际的运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是确立考古遗存中衡量辐辏网络的合适指标,构建实用分析框架,方能有机地整合各类证据,从而更清楚地描绘这些历史联系的完整图景。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