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摸”着日本过河?
新出版的《新消费时代.I,摸着日本过河》一书提及了所谓的“时间机器理论”。这个理论的意思是,在某个发达经济体中发展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乃至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某些进程、反应,在出现在一个发展比它晚一个阶段的经济体中,就会像乘坐时间机器一样回到几十年前,大致予以重现。事实上,在二战战后,日本的战后经济从重建、复苏到走向繁荣,许多方面的特征就复制了美国10-50年前的进程。
《新消费时代.I,摸着日本过河》这本书的书作者认为,考虑到中国与日本在文化认知和地域发展上具有统一性,文明具有相当的共通性(这也是为什么大批中国企业家认同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商业形态具有相似性,所以也可以以“时间机器理论”为据,通过探寻日本过去几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尤其是商业发展特征,结合技术创新的影响,找出中国消费社会的嬗变规律。
作者首先回顾了日本二战战后不同时代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演变。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经济复苏,并因朝鲜战争爆发而迎来了强劲增长,但这一阶段,还没有真正意义上进入民众消费的高峰期,正如书作者所说延续了战前主要由上层阶层人士炫耀性消费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制造业的多项产业走向成熟,实现了大型化、集约化生产,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商品价格,也开始真正意义上塑造出数量庞大、拥有较强消费实力的中产阶级——这一阶段,战后人口增长高峰期期间出生人口走向成年,也成为了社会消费品的中坚消费阶层。该年龄段人群成长于经济增长期,对物质极度渴望,追求差异化和个性化消费,愿意为精神文化消费、娱乐性消费花钱。
值得重视的是,也正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先后经历了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后制造业岗位向海外流失、贫富差距拉大等变化,所以开始为尾货超市、百元店等零售业态的涌现创造空间。我们可以将这些业态视为实体版的拼多多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收到了抑制,之前热衷于股市运作、疯狂融资、疯狂扩张的企业的现金流断裂,这种情况下,从业于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日本消费者的消费实力受到影响。而另一方面,日本制造业企业继续致力于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所以仍然抱有强劲的竞争力。两种因素影响下,日本许多行业都出现了企业并购热潮,行业集中度提高;而受宏观经济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后进入职场的一代人开始面临更强的竞争压力,所以也催生出许多有趣的次生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段出生的人们,更是变得“佛系”了起来,给自己选择的标签是“断、舍、离、穷”,追求节俭,消费冲动被抑制。正如书中指出,日本消费者从追求品牌标签,到追求极致低价,再到追求极致性价比和品质,这个转变对于零售业以及消费品制造业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说完了“人”,再来看“场”,即消费场所(消费行业零售基础设施)。19世纪,百货商场在美国率先出现,并很快扩散到了欧洲国家和日本。二战前,日本就已经涌现出大量的百货店。但在大众消费时代后,日本零售业开始出涌现出新型业态,比如大型综合商超,最典型的即是大荣、伊藤洋华堂。而家电、化妆品等行业,也出现了所谓的品牌直销店。20世纪70年代后,过去红火的大型商超景气不再,日本开始涌现出专卖店、购物中心、便利店开设的热潮,而奥特莱斯(大型折扣聚合商场)、家居建材超市、折扣店以及前面提到的百元店也纷纷登场。近年来,在日本,百货店全面退守,而大型综合商超仍有部分在死守,所谓的“品类杀手店”大爆发,便利店成功登顶,药妆店在少子老龄化时代受到了相当的关注。书中以“全家”、“7-11”等日本连锁便利店的运营特征轨迹为据,对日本零售业业态的演变发展进行了阐述
《新消费时代.I,摸着日本过河》一书指出,日本零售业业态的高频剧变、“场”的高死亡率其实源于人和货加速变化导致的跃迁失败。以大型综合商超为例,其繁荣是因“货”的工作化转型完成,制造业发展成熟,所以在日本居民人均收入提升、消费欲望提升的情况下很好地满足了需求。但这一业态在新生代人群成为消费主力群后就变得不太合乎时宜。
日本的消费降级业态(从大型综合商超转向折扣店、“品类杀手店”、便利店为主),这种状况也会出现在中国吗?书作者首先认为,日本从奢转简,而中国是从无到有,直接照搬日本消费降级业态是不适用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分析日本在这一过程中的消费市场演变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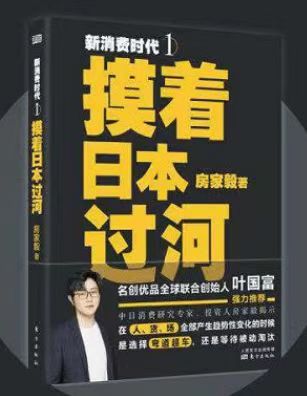
书名:《新消费时代.I,摸着日本过河》
作者:房家毅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8月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