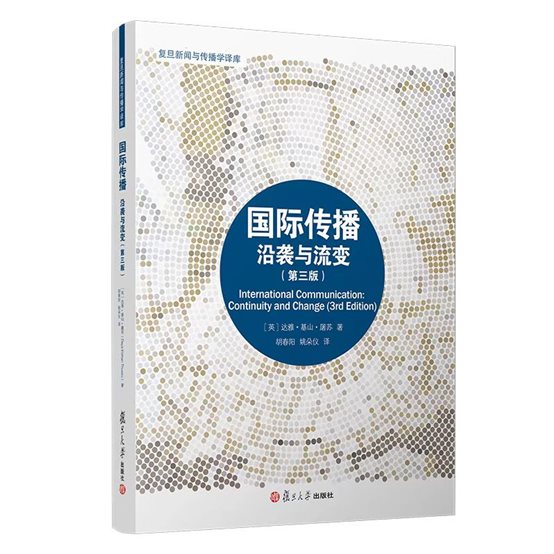
《复旦新闻与传播学译库之国际传播:沿袭与流变(第三版)》
[英]达雅·基山·屠苏 著 胡春阳 姚朵仪 译
2022年1月
侨民文化与“移民”媒介
跨国媒体扩散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的物理移动—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称之为“民族景观” (ethnoscape),即人们从一个地理位置迁徙到另一个地理位置,并携带着他们自己的文化。作为贸易、宗教扩张和移民的结果,文化一直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扩张到殖民主义和去殖民化,都可以看到这个过程。21世纪,英国的南亚人、法国的北非人、德国的土耳其人和美国的拉丁美洲人占居住地人口甚多。大量迁徙发生在南方国家内部。例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口的70%以上是外国工人,其中大多数来自印度次大陆。这使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成为印度传媒组织的主要目标,电视频道、在线媒介端口以及电影发行网络相互竞争,向始终富裕的市场提供文化产品。此外,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多边官僚机构雇用的专业劳动力日益国际化。结果,除了少数例外,21世纪的大多数国家都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许多国家使用多种语言。移民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了自己的才能: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布林(Sergey Mikhaylovich Brin)是来自俄罗斯的移民,而该公司2017年的首席执行官是出生于印度的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微软的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也出生于印度。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6年,世界上七分之一的人口是移民,总共有2.5亿国际移民(包括2 100万注册难民)和7.5亿国家内部移民(World Bank, 2016a)。根据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办事处[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UNHCR),简称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2017年非洲有超过1 140万人在自己的国家流离失所,470万难民和140万庇护寻求者。在整个历史上,冲突是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核心。据联合国难民署称,2016年,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内战或军事冲突频繁的地区,叙利亚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流离失所,其难民人数在全球难民数量中占比最大。尽管移民和难民危机已成为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重大政治问题—被用来获取选举利益(美国的特朗普当选和英国的脱欧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但接纳世界上89%难民的却是发展中国家(World Bank, 2016b)。2017年,土耳其的难
民人口居世界之首,有340万难民和庇护寻求者,其中绝大部分(315万)来自叙利亚;而巴基斯坦是130万登记在册的阿富汗难民的家园,他们占全球220万阿富汗难民的一半以上。联合国难民署称,在非洲,乌干达是最大的难民收容国,难民占该国总人口的3.5%。
尽管移民已经学会了与他们的东道主文化共处,并且大多数社区也基本上接受了他们的存在,但至少在文化上,他们仍然被视为“不同”。然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移民也带来了切实的经济收益:他们寄回母国的汇款超过官方的发展援助。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6年,全球排名前五位的汇款接收国是印度(630亿美元)、中国(610亿美元)、菲律宾(300亿美元)、墨西哥(290亿美元)和巴基斯坦(200亿美元)。而在诸如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和利比里亚等国家,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30%。
南方存在于世界大都会中心,是由所谓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过程带来的,加西亚 · 坎克里尼(Garcia Canclini)将去疆域化描述为“文化与地理—社会疆域失去‘自然’联系”(1995:229),这种现象最引人注目。身份问题对于移民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经常在“不同文化间”生活(Bhabha, 1994)。移民在东道国具有双重身份,同时又渴望成为原籍国文化(有时是一种假想的“家园”)一分子,这二者之间展开对决,使移民容易接受文化杂糅(Anderson, 1991)。正如马丁 · 巴贝罗(Martin Barbero)所论证的那样,文化融合的本质可能导致文化的一种杂糅。
过去,侨民社区使用各种类型的媒介与其母国文化保持联系—从信件、书籍、报纸和杂志,到录音带、视频和电影DVD。卫星电视使跨国广播公司有可能迎合特定地理语言群体(Karim, 2003; Chalaby, 2005)。例如,马来西亚华裔可以接收来自中国的节目,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可以观看阿尔及利亚频道和其他阿拉伯语频道。于1995年由库尔德流亡者在伦敦成立的Med-TV 声称是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喉舌,在土耳其政府的压力下(土耳其政府认为PKK是恐怖组织),该频道于1999年关闭,在比利时又以Medya TV(1999—2004)之名复活,然后转移至丹麦,成为Roj TV(2004—2012)。目前,该频道是库尔德侨民的电视台,不过只以数字形式存在。对此类频道的需求还反映出,主流媒体和国家广播公司为少数族群社区提供的服务是匮乏的。随着宽带技术的革命,只需轻触数字传输设备的按钮,移民就可获得远比从前丰富的内容。
一个普遍的谬论是,此类内容的日益普及促使人们对世界大都会中心的文化差异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促成一种多元文化主义趋势。尽管有些广告商发现这类频道是吸引作为潜在商机的受众的有用手段,但通常得不到东道国多数成员的关注,这进一步导致了受众的分散和少数族群的贫民窟化。对于移民及其家庭而言,正在发生的传播与信息技术的革命—“众多互联网和移动平台的出现,例如电子邮件、即时消息(IM)、社交网站(SNS)和通过互联网语音的网络摄像头协议(VOIP)”—都改变了其媒介消费方式,并使“互联的跨国家庭”享受所谓的“多媒体”世界(Madianou and Miller, 2012: 1)。
互联网媒介的影响力也改变了国际传播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这是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
互联网与政治传播
互联网的商业化曾被欢呼为民主的甚至是颠覆性的传播工具,但一些人认为,它背叛了创造一个“全球公共领域”和另类论坛的初衷。在早期,互联网被视为一种大众媒介,其基本原则是基于对免费信息的访问以及去中心化的信息网络。对于许多人来说,互联网开辟了全世界数字对话的可能性(Negroponte, 1995; Cairncross, 1997),并且最大程度上推动了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来的言论自由。在线传播与传统传播不同,传统传播遵循自上而下的一对多模式,而在线传播是一种多对多的对话,因此在本质上更加民主。在数字媒介世界中,消费者可以创建自己的内容并将其分发给全球受众。虽然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没有免于世俗与平庸,但通过社交媒介进行的政治传播也有了非同寻常的增长(Benkler, 2006; Shirky, 2010, 2011)。
这也影响到全球公共传播。正如沃尔克默(Ingrid Volkmer)所指出的那样:“互联性不仅存在于‘当地’(localities)之间,也存在于‘观察者’和‘行动者’之间。‘行动者’与不断打磨的语境结果以及‘事件’的‘意义’进行直接‘现场’(live)互动,通过这些互联性的主观节点对相关性进行‘重新排序’(reordering)。”(2014:8)在信息系统仍然被不那么民主或不民主的政权控制的国家,博客博主的作用非常重要,例如在伊朗(Sreberny and Khiabany, 2010),或阿拉伯国家(Howard and Hussain, 2013; Khatib and Lust, 2014; Kraidy, 2016)。然而,这种互联性也为极端主义组织提供了一个平台,从以电子方式传播纳粹商品和仇恨宣传,到毫不犹豫地在其网站上展示斩首视频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Archetti, 2013; Simpson and Duxies, 2015; Aly et al., 2016)。五花八门的利益群体、装备和虚拟社区越来越多地在网络上诞生,正在创造另类的叙事与网络(Downing, 2001; Atton, 2004)。这一趋势始于1994年世界上第一个“信息游击运动”—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Zapatista),这是一场争取在墨西哥的恰帕斯州(Chiapas)实现自治的运动,其领导人司令官马科斯(Marcos)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运动中利用互联网而成为国际英雄的,该运动已被世界各地其他激进团体与运动所复制、扩展(Castells, 2000b)。
互联网已经成为促进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社团之间以及政治活动家之间联系的一种关键手段(Earl and Kimport, 2011; Bennett and Segerberg, 2013; Howard and Hussain, 2013; Shah et al., 2015; Mutsvairo, 2016; Segura and Waisbord, 2016)。这方面的早期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的“反全球化运动”(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s),该运动利用在线动员获得国际支持,以反对多边投资协议以及反对公司控制全球贸易的增长趋势,导致世界贸易组织于1999年在西雅图举行的部长级会议陷入僵局,随后的世界银行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以及七国集团年度峰会都陷入僵局。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是一个各种民间社会团体的联合组织,自2001年以来每年举行会议,推动“改变全球化”。诸如此类的一些组织已扩大到包括Change.org和美国的Avaaz组织,这是一场“全
球网络运动,旨在用人民主权的政治推动各地的决策”。Avaaz自2007年投入运营以来,在10年间收获了超过4 700万的全球会员。虽然它声称自己没有政治偏见,但在其开展的一些国际活动中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特别是在美国2009年大选期间,向反伊朗政府支持者提供了代理服务器;为2011年利比亚反卡扎菲(Ghaddafi)叛乱提供了培训和传播设备;未经叙利亚政府批准,派西方记者前往叙利亚报道战争。
互联网政治也在新型行动中发挥了作用:瑞典海盗党(Swedish Pirate Party)就是一个例子。该党于2006年出现,当时一群软件程序员和文件共享极客们抗议警察压制瑞典的海盗湾(The Pirate Bay)—海盗湾是瑞典一个文件共享搜索引擎。随后发生的其他类似例子有德国海盗党(German Pirate Party),其特征是呼吁“自由文化”(free culture),这与欧盟的“网络自由运动”(cyber-libertarian movement)法律体系相冲突(Burkart, 2014)。在西班牙,2011年发生的“愤怒者”(los indignados)运动要求“真正的民主,立刻!马上!”,这个口号呼应了美国发生的占领抗议活动中所提出的“我们是那99%”(Castells, 2012)。基于互联网的传播网络对“网络左派”(cyber left)发挥的作用也至关重要,正如印度媒介(Indymedia)的案例所示—它是“全球社会正义运动”(Global Social Justice Movement)的一部分,经过十多年的全球运行后,于2012年停运(Wolfson, 2014)。2012年,《科尼2012》(Kony 2012)纪录片在线发布,凸显了乌干达军阀约瑟夫 · 科尼(Joseph Kony)所犯下的暴行,尤其是针对“儿童兵”的暴行,在推特信息流和名人支持的几周内获得了国际响应:截至2017年,该纪录片的观看量已超过1亿次(Meikle, 2014)。同样的,2016年,美国当时的第一夫人米歇尔 · 奥巴马在社交媒介上发布了自己的照片,标签为“#把我们的女孩还给我们”(#BringBackOurGirls),指的是2014年在一所学校被绑架的276名女孩,绑架实施者是尼日利亚一个激进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这引起了人们对这些女孩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其全球影响力相当可观。 推特成立于2006年,已成为政治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介,每个政治家或团体都使用它与支持者沟通,名人用它与粉丝沟通。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案例:一个推特标签将活动家和普通市民聚集到一起,去追求共同的政治目标,从而增强了贝内特(Lance Bennett)和塞格伯格(Alexandra Segerberg)所说的“数字网络化的联结行动(connective action),该行动使用具有广泛包容性、易于个人化操作的行动框架,这些框架是技术辅助网络化的一个基础”(2013:6,黑体为引文所注)。他们认为,“技术支持的网络”,“本身可以成为充满活力的组织”,从而“作为组织来传播”(communication as organization,p.8,黑体为引文所注)。标签已被有效地用于社会运动,例如“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然而,一些学者认为,标签行动主义是一种“懒人行动主义” (Slacktivism)形式,因为它关乎的是人们在安稳的家里上网谈论的东西,而不是真实地采取行动。“懒人行动主义” 通常用于描述旨在进行政治或社会变革的在线行动,但极少做出参与的努力,如注册一场在线请愿或加入一次社交媒介讨论。
其他一些人认为,数字媒介技术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往往被夸大了。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认为,尽管存在与在线行动主义相关的炒作,但互联网并不是特别适合大规模的政治活动,因为互联网的大多数用户是出于非政治原因而参与互联网的,他们消费、分发或制作的是诸如“跳舞的猫”这样的内容,而不是政治素材。他认为,通过在线而组织起来的任何成功行动主义实例都是“偶然的,只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确定性,而不是一项真正的成就”(Morozov 2011: 180)。尽管西方话语和媒体报道众口一词地夸大社交媒介的作用,但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期间,在那些动荡的时刻,在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家—埃及,使用推特和脸书的人数却极低:2011年3月,只有0.001%的埃及人口使用推特,这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评价的那样,“不过是以一种西方视角,通过西方技术的棱镜来看非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Fuchs, 2014: 180)。一些学者把“阿拉伯之春”看作是独裁政权传统统治地区民主化的预兆(Howard and Hussain, 2013)。然而,同样不假的是,在那个时期反抗诸多阿拉伯国家政体的抗议中,社交媒介是引发泛阿拉伯国际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Khatib and Lust, 2014)。
所谓的“反恐战争”也在数字领域展开:伊斯兰国家对社交媒介的利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Farwell, 2014; Atwan, 2015; Stern and Berger, 2015)。一些人认为,由于新技术能够实时塑造公众对冲突的看法,通过社交媒介进行的“叙事战争”(narrative war)变得比实体战争更重要。社交媒介的传播带来了“虚拟大规模征兵”(virtual mass enlistment) 的情况,这种情况为平民提供了与国家宣传机器一样多的权力(Patrikarakos, 2017)。但是,关于代理的论调可能无法得到关于冲突报道的既有事实的证实。乔治 · 华盛顿大学为美国和平研究所(US Peace Institute)制作的一份关于叙利亚社交媒介的报告指出:“社交媒介创造了
一种关于无中介信息流动的危险错觉。那些关注油管视频、叙利亚推特账户或脸书帖子的人可能会认为他们正在收到有关冲突的准确而全面的报道。但这些流动是由活动家网络精心策划与设计的,旨在制作特定的叙述。实际上,社交媒介网络中的关键策划中心现在可能发挥着一种守门作用,而这个作用和当年电视生产者和报纸专栏编辑扮演的角色一样强劲有力。”(Lynch, Freelon and Aday,2014: 6)
政府在部署社交媒介方面的作用也不应低估。美国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部副部长理查德 · 斯坦格尔(Richard Stengel)于2015年担任国务院战略反恐传播中心的首脑,他用一篇英语推特推文“想想还是算了吧”(“Think Again Turn Away”)来反击“伊斯兰国”组织(ISIS)的招募宣传。斯坦格尔告诉《广告时代》:“最终的战斗不是在军事战场上,而是在信息空间……我们需要在这场公关战中招募广告和营销方面的专家、能人与干将。”(Bruell and Sebastian, 2015)还有人认为,大多数“在线集体行动”的尝试可能有助于动员,但其有效性仍然值得怀疑,这就说明,“数据科学”和“用社会数据做实验”可以对这些行为作出更好的理解(Margetts et al., 2015)。正如富山健太郎(Toyama Kentaro) 所说的那样:“缺陷不在技术或技术官僚本身,而是我们对他们将要实现什么样的社会变革持有错误的、过于乐观的信念。”(2015:217)
社交媒介的政治化也受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影响,这些组织在国际互动、政策影响和媒体话语影响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推动在线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Willetts, 2011)。然而,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是国际性的组织,但许多组织代表并反映了西方对全球问题的看法,有些人甚至沉浸在殖民主义思想中—一项对英国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发现,他们的信息投射出“诸多殖民话语”(Dogra, 2012)。在更正式的政治传播中,互联网也极大地影响了政治话语。政党利用社交媒介操纵选举进程以赢得选举。美国总统唐纳德 · 特朗普使用他的推特账户来竞选,并与其团队和数百万粉丝进行沟通,这是一种新型“数字蛊惑”(digital demagogy)骇人听闻的例子(Fuchs, 2018)。在2013年的意大利大选中,作为博客博主、由喜剧演员转变为政治人物的贝佩 · 格里洛(Beppe Grillo)及其“五星运动”(Movimento 5 Stelle)采用了将新技术与老式行动主义相结合的策略,赢得了25%的全国选票。他使用了“网络民主”这个概念以及诸如脸书、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介,以便吸引身处这种语境中的大多数人,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开展互联网政治行动最为精彩的案例”(D’Arma, 2015)。
在更大规模上,于2014年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之一—印度举行的选举中,纳伦德拉 · 莫迪(Narendra Modi)掌权,而部署社交媒介是竞选的核心。作为全球第一次,“莫迪还在一场‘同时在150个地点’召开的3D竞选集会上,以一幅全息图像发表演讲;而政治活动家和政党工作人员的一支网络军队正在使用多种数字平台和应用程序,以多种印度语言管理并发送有关竞选的讯息”(Ullekh, 2015: 4)。
在西班牙,由巴勃罗 · 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等学者于2014年发起的“我们可以”(Podemos)运动创建并使用了在线新闻网站“我发表”(Publico)来推动他们的事业(Tremlett, 2015)。在英国公关公司贝尔 · 波廷格(Bell Pottinger)的支持下,网络喷子(internet trolls) a也利用社交媒介平台来捕捉南非的种族紧张局势,以回击来自前总统雅各布 · 祖马(Jacob Zuma)的批评(Wasserman, 2017)。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地方,使用数字技术的公民媒介运动和传播活动家为制定一个更民主、更多元化的媒介政策做出了贡献(Segura and Waisbord,2016)。
互联网也以更具创新性的方式用于政治传播。例如,2011—2012年,俄罗斯的互联网在线论坛发出另类的反对声(Oates, 2013)。在中国,博客在中国互联网上呈指数级增长。例如用户生成内容的流行视频平台bilibili,民众可以在其中创建个性化频道,发布实时评论,发送私人信息。这种联通性用于抵制美国主导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现实的歪曲。关于数字媒介的这种使用,有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2008年为了回应西方的不公正报道,网民们创建了一个叫“anti-cnn.com”的网站(Jiang, 2012)。
案例研究:“假新闻”的全球化
考虑到全球化传播环境中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基于互联网的新闻媒体也遭遇了准确性的挑战—无论是事实还是语境。在急于首发新闻时,主流新闻营运者与数字新闻提供者以及非国家行动者展开了竞争。这种联通性被极端主义团体滥用,破坏了新闻业: 《时代》杂志于2016年用一个封面故事解释了“为何我们让互联网在仇恨文化面前败下阵来?”。2017年,一份题为《信息失序:迈向研究和决策的一个跨学科框架》的报告(The Information
Disorder: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Making)警告说,在这种数字环境中存在新型的“全球信息污染”,该报告受欧盟委员会指派,并与首稿(First Draft)以及哈佛大学媒介、政治与公共政策舒伦斯坦研究中心(Shorenstein Center on Media,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合作完成。“全球信息污染”来自“一张创造、传播和消费这些‘污染’信息的复杂动机网络;无数的内容类型与夸大内容的技术;无数平台托管和复制这些内容;以及在可信赖同伴之间极危险又高速的传播”(Wardle and Derakhshan, 2017)。它确定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信息失序(information disorder):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是指共享了错误信息但没有造成伤害时;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是指明知是错误信息还分享并造成伤害时;不良信息(malinformation),是指共享了真实信息并造成伤害时,通常是把私密信息放进公共领域里”(p.5)。
在国际新闻界,西方媒体还指控肇始于俄罗斯的假新闻—“虚假讯息”(dezinformatsiya)(Pomerantsev, 2015)。一个突出例子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人们见识了这种信息失序,非传统媒体似乎形塑了竞选话语(Silverman, 2016)。其他研究,特别是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证实了右翼网络出版物如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在制定选举议程中的作用(Benkler et al., 2017)。
在美国之外,许多国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现象。牛津大学的牛津互联网研究所进行的计算宣传研究项目,研究了 “算法、自动化以及人工策展”的使用,“旨在有目的地在社交媒介网络上分发误导信息”;该研究揭示了计算宣传在2014年巴西总统选举中以及在对前总统迪尔玛 · 罗塞夫(president Dilma Rousseff)的弹劾中所发挥的作用;乌克兰在社交网站VKontkte、脸书和推特上对乌克兰公民发动了在线虚假信息活动,这些研究者称之为“可能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记者和新闻业的实践活动。在文本、数据、音频和视频融合的多媒体环境中,记者可以用更具吸引力的方式去讲述他们的故事。通过是全球最先进的计算宣传案例”。根据他们的研究,“最强大的计算宣传形式涉及算法传播和人工策划—机器人和网络喷子合作完成”(Woolley and Howard, 2017)。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操纵行为甚嚣尘上,专业媒体组织由此提高了警惕,专业媒体组织的可信度因社交媒介的压力而受到侵蚀。在假新闻问题出现之后,美国和欧盟出现了大量的事实核查组织(Graves, 2016),仅欧盟在2016年就有34个事实核查业务,其中大部分都是非营利组织(Graves and Cherubini, 2016)。政府也已做出了一些努力来应对从俄罗斯发出的网络信息战。2015年,欧盟各国政府成立了“欧洲对外行动服务局东方战略传播行动组”(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ast StratCom Task Force),旨在挑战俄罗斯的“虚假信息”,该机构一直在运行一个叫“欧盟对虚假信息” (EU vs. Disinformation)的网站,是一场更好地预报、解决和回应亲克里姆林宫的“虚假信息”运动的一部分。该组织与其合作伙伴通力合作,每周都会制作一份《虚假信息评述》(Disinformation Review),借由该评述, 2017年之前它已经确定并汇编了3 500多起虚假信息案例。
人工智能也可用于处理日益增长的假新闻,乱喷和无节操的在线传播比清醒的分析更能获得“点击”。因此,在线服务提供者几乎没有动力去阻止这些话语,因为这些话语会促进浏览与评论,并有可能成为病毒性传播。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主义宣传)、恶作剧的(政治竞选)或简单的错误信息(业内的意见领袖)—无论是由人类还是机器人操作的信息机器生成的—都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予以监控和调节。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分析了2006—2017年超过300万人发布的126 000个被验证为真实的和虚假的新闻故事,他们发现虚假的东西比真相传布得更远、更快、更深、更广(Vosoughi, Roy and Aral, 2018: 1146)。其他人则表示,推特还“培育了基于广泛弱联系网络的创新社会形态,这些网络在灾难期间使世界保持信息更新,或通过众包集体智慧帮助解决问题”(Murthy, 2013: 153)
全球传播:隐蔽的监视与公开的监控
控制国际信息的斗争一直是国际传播的一个关键主题。如第1章所述,国际传播手段(电缆和无线电)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在冷战时期发射的卫星中有70%以上用于防御,而两个超级大国都使用卫星来监视彼此的核能力。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军方意识到信息传播技术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武器,特别是与“心理打击”(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PSYOPS)(Taylor, 1997: 148)相关,后者越来越多地在网络战中以电子方式进行。先进的间谍卫星提供有关“信息战斗空间”(information battlespace)的信息,而无人驾驶的电子战机会对敌人的雷达进行干扰或提供虚假图像,以及阻挡或拦截数字传输。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炸弹”和病毒把敌人的计算机系统搞瘫痪,特别是那种运行着一国之金融网络的
系统。到20世纪末,美国陆军已经开发出了一种电子“陆地勇士”(Land Warrior)。在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期间(被称为互联网上的第一场战争),来自双方的黑客扰乱了塞尔维亚和北约的网站,而美国的“信息打击”(Information Operations)把南斯拉夫政府的电子邮件系统搞瘫痪了。
美国国家安全局领导了一项名为埃施朗(Echelon)的广泛国际监控行动。通过间谍卫星和数字监控设备的组合,它可以拦截移动电话呼叫,并从敏感的监听站窃听国际电子传播—电话、电传、电子邮件和所有无线电信号、航空公司和海事频率。在和盎格鲁—撒克逊主要国家(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 签订一份秘密协议后,埃施朗系统于1948年成立,其主要基地位于英国的曼威斯山(Menwith Hill)和莫文斯托(Morwenstow)、太平洋沿岸的亚基马(Yakima)和美国东海岸的舒格格罗夫(Sugar Grove)、加拿大的利特里姆(Leitrim)、澳大利亚的浅滩湾(Shoal Bay)和杰拉尔顿(Geraldton)以及新西兰的怀霍派(Waihopai)。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合作,在英国的曼威斯山建立了最大的电子间谍基地,为美、英在采购、处理国际情报与传播方面提供竞争优势。监测伊斯兰激进分子是全球监测机构的一个主要焦点。在私有化的全球传播环境中,卫星图像行业与国防部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后者利用商业公司的卫星情报,如1994年成立的美国公司—空间成像(Space Imaging)公司。该公司由洛克希德 · 马丁公司、雷神公司以及谷歌地球公司所创建,这些公司从这个商业化、高利润的全球卫星成像市场中赚得盆满钵满。
美国卫星与互联网运营商在如下领域有着突出地位:侦察、监控和成像系统以及整合空间、空中和地面信息与传播系统,这就确保了美国对国际传播的控制—“全频谱统治”(full spectrum domination),这种控制既是软娱乐的,也是硬军事的。欧盟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对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的依赖,开发了自己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第一颗卫星于2005年发射。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LONASS),中国开发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数字联通的这种增长已经改变了全球监视与监控,并迫切需要对信息资产与传播系统保障网络安全。正如帕斯奎尔(Frank Pasquale, 2015)所说,个人在线行为的“诸点被公司连接起来”,这是通过复杂而有效的算法来跟踪、存储和交易数据来完成的,而这些数据可用于制造或破坏声誉、经济、政治与社会过程及结果。除了这些数据挖掘者,强大的国家、非国家行为者和非政府组织也参与了网络宣传和黑客攻击,这引起了人们对数字领域安全的担忧(Franklin, 2013)。随着“物联网”开始变得更加稳固,国家、公司和个人越来越急于保护他们的网络资产(US Government, 2014)。据研究公司加特勒(Gartner)称,2013年全球各地的组织在信息安全方面花费了670亿美元。尽管对电网与传播网络,有人认为应担心网络战或恐怖袭击(比如一场“网络9 · 11”), 但有人却认为,真正的威胁是间谍、破坏与颠覆(Rid, 2013)。
然而,被指控进行数字破坏的不是无国界的恐怖主义组织,而是民族国家的政府。一个早期例子发生于2007年,据称当时俄罗斯对爱沙尼亚发起了网络攻击,爱沙尼亚的传播与互特网网络瘫痪,生活秩序遭到破坏;该国由于实施其“电子斯托尼亚”(E-Stonia)项目,而成为电子联系最紧密的社会之一(Pomerantsev, 2015)。另一个突出例子发生于2010年,当时美国和以色列“软件专家”的“大作”,“被称为震网(Stuxnet)的一个计算机程序,破坏了伊朗的核设施离心机”(Economist, 2014)。俄罗斯涉嫌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前面提到的黑客行动,这些行动揭示了网络的破坏性以及干扰西方民主进程的潜力(Soldatov and Borogan, 2017)。
美国、以色列、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涉嫌开发、部署网络武器。一些非西方国际日益主张重塑网络领域,旨在挑战西方对这一领域的统治地位。曾为英国对外情报局军情六处(Military Intelligence 6, MI6)工作的因克斯特(Nigel Inkster)提出,西方将被迫适应这样一个世界:其技术优势正在迅速消逝,并且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Inkster, 2016)。随着网络空间成为地缘政治的新的前沿阵地,各国政府赞助、部署和利用黑客—“网络代理人”(cyber proxies)—作为投射或保护国家利益的渠道,在这方面政府已成为企业家(Maurer, 2018)。
斯诺登事件是最突出的例子,揭示了在一个民主而自由的互联网中,大规模监控的存在(Greenwald, 2014)。《华盛顿邮报》进行的一系列特别调查(后来出版成一本电子书),揭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实施的广泛监控计划以及全球范围内移动电话跟踪系统。这使隐私问题凸显出来。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工爱德华 · 斯诺登称,互联网是一部“监视你的电视”,并指责政府“秘密滥用(它),超越了必要、适当的权力”(Washington Post, 2014)。特别引起争议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PRISM)计划,该计划允许美国情报机构从谷歌、脸书和苹果等公司获取信息。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还显示(The NSA Report, 2013),在《外国情报监控法》的框架下,美国政府收集了“位于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的“电子传播内容,包括电话和电子邮件”。
众多机构正在“清空那些他们曾经筛选、分类和存储的数据”, 美国国家安全局只是其中的一个(Andrejevic, 2013: 1)。其他人已对监控状态下新闻业的未来表示担忧(Bell and Owen, 2017)。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指出,这种对“个人信息和个人传播内容空前规模”的监控也“损害了美国在国际上倡导互联网自由的可信度,而至少从2010年开始美国就将互联网自由列为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Human Rights Watch, 2014: 3)。
学者们认为,既然互联网具有“全频谱监控和信息中断”潜力,人类战争演变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利用控制论(cyberneticsa),并且,美国已经为网络战做好了充分准备(Singer and Friedman, 2014)。根据安全公司思科的说法,垃圾邮件占全球电子邮件总量的近三分之二并且还在增长,“2016年观察到的全球垃圾邮件”高达10%“可归类为恶意邮件”(Cisco, 2017: 5)。根据美国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赛门铁克(Symantec)发布的《互联网安全威胁报告》(Internet Security Threat Report, ISTR),诸如恶意软件、垃圾邮件、网络钓鱼和勒索软件,以及加密数据挖掘器等网络风险正在全球范围内稳步增长;美国是最脆弱的,2017年,它所记录的威胁占全球的26%以上;其次是中国和印度(ISTR,2018)。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能力的全球化有助于强化快速的全球传播—例如进行机器翻译,或推进医学图像分析。然而,部署在监控、政治宣传和媒体操纵中的人工智能也开始影响国际传播。2018年,来自西方顶级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包括电子前哨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专家撰写了一份报告《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预测,预防与缓解》(The Malicious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ecasting,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该报告审查了三个安全“领域”(数字的、物理的和政治的)。它研究了人工智能如何通过篡改视觉内容来平衡或操纵政治传播。报告指出,“利用人工智能可以使监控任务(例如分析大量收集到的数据)、说服(例如制作有针对性的宣传)以及欺骗(例如操纵视频)自动化,这可能会扩大与隐私侵犯、社交操纵相关的威胁”(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2018: 6)。发表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的另一项研究警示了机器控制的后果,研究指出了人们 “更为成功地进行着远程控制”,并且趋势是:正在用一种“数字权杖” (digital scepter), “从监管计算机到监管人”;这个权杖使人们能够“有效地治理群众,而不必让公民参与民主进程”。该研究指出,其基本要求是“整合、收集数据并进行传播”。把人和物都连接到“万物互联网”(Internet of Everything)是获取所需数据的理想方式,只管输入网络控制策略就可以了(Helbing et al., 2017)。
复旦新闻与传播学译库
国际传播:沿袭与流变(第三版)
[英]达雅·基山·屠苏 著 胡春阳 姚朵仪 译
2022年1月
注意力分散时代:高速网络经济中的阅读、书写与政治
[澳]罗伯特·哈桑 著 张宁 译
2020年6月
习以为常: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
[美]理查德·塞勒·林 著 刘君 郑奕 译
2020年2月
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
[丹麦]施蒂格·夏瓦 著 刘君 等译
2018年6月
被误读的麦克卢汉——如何矫正
[加拿大]罗伯特·洛根 著 何道宽 译
2018年4月
社交媒体:原理与应用
[美]帕维卡·谢尔顿 著 张振维 译
2018年4月
新媒体批判导论(第二版)
[英]马丁·李斯特等 著 吴炜华 付晓光 译
2016年8月
新媒介:关键概念
[英]尼古拉斯·盖恩 戴维·比尔 著 刘君 周竞男 译
2015年8月
新新媒介(第二版)
[美]保罗·莱文森 著 何道宽 译
2014年7月
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英]尼克·库尔德利 著 何道宽 译
2014年5月
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
[丹]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著 刘君 译
2012年9月
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
[加]罗伯特·洛根 著 何道宽 译
2012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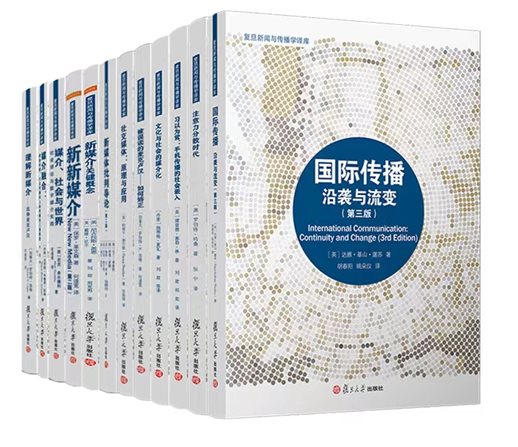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