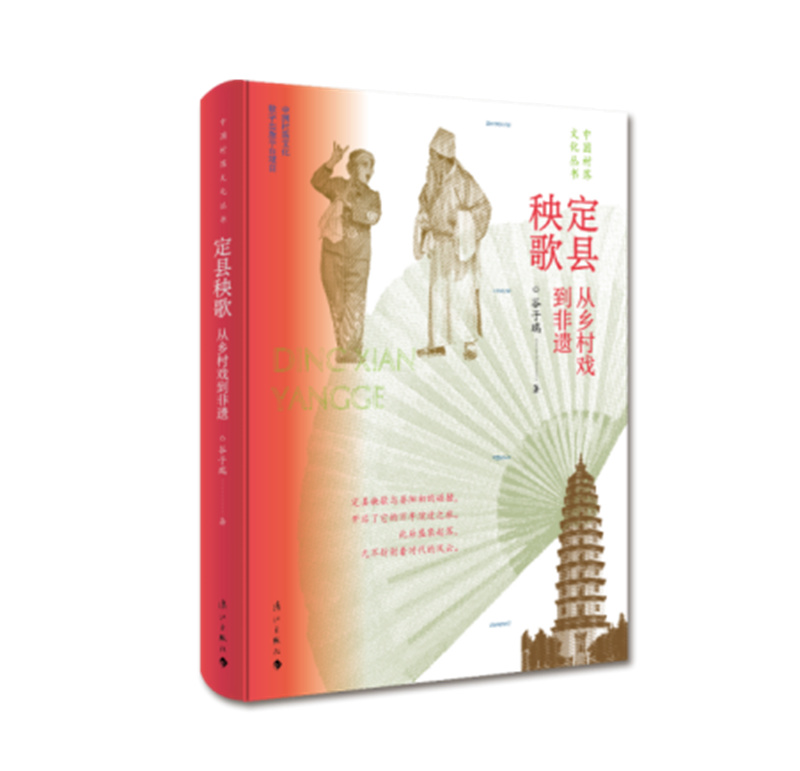
《定县秧歌:从乡村戏到非遗》谷子瑞著/漓江出版社2022年10月版/68.00元
因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倡导和实践的平民教育运动,定县驰名中国,也有了世界性的意义。正是在这一“洋博士下乡”的乡村建设以及民族自救运动中,定县秧歌进入这些洋博士的视野,且凸显了出来。1933年,作为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中坚,李景汉、张世文一道选编了《定县秧歌选》,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出版。数十年后,深度参与了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美国人甘博,出版了定县秧歌的英文版。
自此,定县秧歌这种原本在乡野生发、传衍的小戏,不再仅仅是民间、乡土、方言与日常的,它与知识精英、城市、民族国家、政治、教育、文化、艺术审美、遗产、治理术、跨文化交际和世界等,都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
因为平教会诸君的关系,作为《定县秧歌选》主要的信息源,秧歌艺人刘洛福1931年前往北平登台献艺,并灌制了唱片。作为乡村戏,定县秧歌既是平民教育的媒介,也因之成为始终被赞誉有加的成果、经典。在当地的抗战动员、社会主义新人塑造、改革开放后的社会重整、红白喜事及庙会节庆等日常生活和当下的非遗运动中,定县秧歌这一被发现、动员以及主动请缨的乡土文艺,都不同程度地延续了其功能性效用,发挥着其或有形或无形的工具理性。
近百年来,正因为与演-观者日常生产生活、个体生命历程、社会运动、历史演进、地方文化建设、国家大政方针和科技革新之间的复杂互动,定县秧歌始终在学界有着热度。除李同民、李景汉、张世文、甘博、赵卫邦等人的奠基性著述之外,朱迪丝、欧达伟、董晓萍、江棘等他者对定县秧歌都有可圈可点的著述:或偏重剧本,或偏重艺术,或偏重乡民的伦理道德观,或偏重女性在秧歌内外的在场。虽然风格各异,与定县秧歌的演-观者有着不同程度甚至有意的“间离”,但这些主要依托定县秧歌剧文、剧情的著述却多少都基于或长或短、深浅不一的田野调查。
正是在田野调查这个意义上,作为定县本地人,年轻学者谷子瑞这本更偏重活生生的人的《定县秧歌》,显然有着其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价值。
子瑞对定县秧歌从乡村戏到非遗百年小史的梳理,在赋予定县秧歌以脉动——生命迹象的同时,还给我们呈现了他者难以捕捉到的定县秧歌演进的隐蔽语本和其左冲右突的倔强。
其实,写这本不瘟不火也不担心惹人恼而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真心诚意向定县秧歌和故乡致敬的小书,子瑞并不容易。与她的定县秧歌和故土定县一道,子瑞本身也经历了化蛹为蝶的升华和心灵的净化。这种升华、净化,不是渐行渐远的背井离乡,而是对乡野的回归、亲近,直至水乳交融。
我想,经过了成人礼的子瑞一直在喃喃自语:“渺小与伟大同在。乡土在、故土在,人心在、人性在,一切皆有可能!”
料峭春风吹酒醒。无论阴晴、真假,非遗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定县秧歌永远都会是一个问题!(本文为节选)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