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读完中央编译翻译服务组新译的荣格《个体成长心理学》后,我头脑中自然涌现出这句广为流传的话。虽然这句话并非某位特定心理学家的独立观点,但它反映了人们对“童年影响一生”的普遍理解,荣格更是深刻地阐明了这种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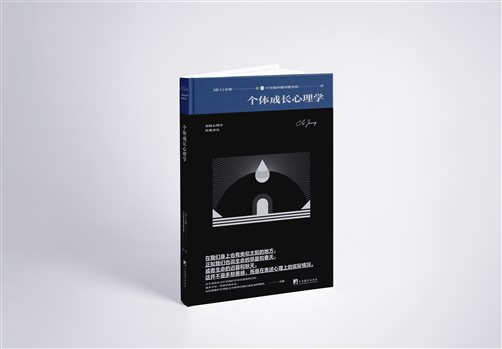
该书由三个相对独立的篇章《人生的阶段》《父亲对个体命运的重大意义》与《一个学生的爱情故事》构成,它们均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共同规律:“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就是一个人的宿命。”一个人无论在人生道路上走多远,都脱离不了这些与生俱来的原始力量的支配。年轻人读这本书,可以“回望来时的路”,有助于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并促进自我人格的成长。迈入中年的我再读这本书,通过人生经历来回溯并检验荣格百年前对人性的洞见,阐幽明微之处不禁让人拍案叫绝,读这本书就好比是“走一条回家的路”。
一、人生的阶段
荣格认为,婴幼儿阶段大抵是不会有精神问题的,因为他们还沉浸在天性中,处于潜意识的状态,亦即生活在本能庇护之下的个体是不会遇到精神问题的。个体在长大的过程中就会背离本能,拒绝本能之后才会产生出意识。精神问题总是伴随着意识的增长而产生的,这也是文明带来的馈赠。荣格指出,“在生命的头几年里我们并没有连续的记忆,最多只有一些意识的小岛,它们就像茫茫黑暗之中的些许孤灯或发亮的物体。”当人们说“认识”某种东西时,实质是成功地将新的感知和其已有的背景内容建立了联系。通过这一途径,人们不仅对新感知的事物有了意识,而且对已有的背景也有了意识。从本质上来讲,感知到精神世界多种内容之间的关联,就是“认识”的基础。譬如,幼儿开始使用第一人称提到自己时,其自我就萌生了。连续的记忆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一阶段开始的,其本质上就是自我记忆。
依据荣格的观点,意识的第一阶段,存在于只能认出或者“认识”的阶段,这也是一种混乱的、无序的状态,就如同上段提及的婴幼儿阶段。人生的第二阶段,是自我情节发展的阶段,这是一种专制的、一元性的状态。例如,青春期的青少年,因为精神与生理上的双重变化使其自我得到很大发展,导致其在这一时期总是毫不吝惜地肯定自己,毫无半点谦虚。这个阶段有时被称为“让人无法忍受的年龄”。人生第三阶段又把意识向前推进了一步,个体能够意识到一种割裂的或者说二元的状态,荣格着重探讨了这一阶段。他认为,精神问题的产生是由于自我内部的分裂导致的。当第一个自我,与第二个强度相当的自我同时出现时,就会产生自我分裂的问题状态。他认为所有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个体或多或少地对童年意识持有执念,而对那些推动其卷入世界的内在或外在的强大力量产生抵触。成年人遭遇精神困扰的共性,就是他们总想把青年期的心理带到下一个时期。老年人若将自己前半生的法则和天性目标带入后半生,那么他必将付出灵魂受损的代价。荣格引用一句法国谚语来总结这种情况:“如果年轻人有经验,老年人有精力,世界将更美好!”
不过,荣格也指出,精神问题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其实并不在于最终解决了问题,而在于我们持续解决问题的过程,正是这一持续过程才能使我们免于厌倦和惊恐。这正是荣格对人类克服精神问题的积极视角。
二、父亲对个体命运的重大意义
荣格在这一部分中指出,塑造我们命运的那股力量有着很强的自主性。在人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它的强大。这股力量的化身首先会体现在父亲身上,因此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神明形象”都根植于父亲意象(Father-imago)。但是荣格并不认为这种力量仅仅属于父亲本身,他认为这是人类在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天生的井然有序的系统,就如同鸟类的筑巢和迁徙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一样。他指出人类生来就带着天性,不仅带着个体的天性,而且还带有集体的天性,此即其集体潜意识理论的萌芽。荣格把这种先天存在的,依靠本能感知的模型或行为模式称为“原型”(Archetype)。
潜意识地认同某种原型是非常危险的。父亲的原型先天就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中,父亲力量的秘密也蕴藏在原型之中。荣格通过剖析4个病例,认为有一种力量在顽强地抵抗着人们的理性和愿望,其本质就是情节冲突。幼儿时期家庭关系的力量就能为这些病例提供有说服力的分析,因为父亲可以潜移默化地将这种影响渗透到孩子的灵魂中去,利用孩子的无知,企图让他们变为情结的奴隶。往往敏感的孩子还没有来得及在精神上反映出父母的过分行为就产生了和父母一样的情感,且他们会将自己的命运归咎于自己的性格。孩子小的时候,父母是最早将人类神秘而强大的法则传授给他们的人。
在研究组织威权管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受威权教养的孩子,会把在家中与父亲形成的(偶尔也是母亲)关系互动模式迁移到成年后的职场中,继而来与上级进行互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组织就是家的延伸。因此,为了人类社会未来更加美好,我们(尤其是父亲)就应从改变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开始,以使其形成现代化的权力互动图式。
三、一个学生的爱情故事
爱所包含的问题包罗万象,十分复杂。荣格先论述了对父母的爱、对子女的爱、对邻居的爱、对国家的爱以及对人类的爱等普遍性的爱,然后才讨论到夫妻之爱。这就意味着爱离开了精神领域,进入到精神和本能的中间地带。带着性欲之火的爱,在前述普遍性的理想之爱中,掺杂了对个人权力、占有欲及统治欲的强烈渴望。但是荣格并没有贬低带有本能的爱,相反,他认为爱越吸收本能的力量,就越美好、越真实、越强大。
他讨论了大学生结婚等议题,虽然受到当时历史文化背景的制约,但其中不乏对人性深刻而富预见的揭露。但荣格思想的局限性经过时间的洗礼也展现了出来,如他认为的“刻意不要孩子的婚姻总是成问题的”“孩子是夫妻双方最好的黏合剂”等,在今天看来已不合时宜。
自荣格1921年出版令其名声大振的《心理类型》一书已逾百年,然而,百年后的人类对精神问题的智慧还大致停留在荣格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步。这也许与当今世界对科学主义的极度推崇不无关系,可自然科学在面对人类精神甚至是意识问题时,还表现得较为乏力与无效。韦伯在上个世纪初宣称科学的任务就是“给世界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d),仅半个世纪之后,哈特曼等人就提议给科学祛魅,这意味着客观性作为一种理想的魔幻魅力已经给除魅(Disenchanted)了。在应对人类的精神问题时,我们当然需要科学,但是不要科学主义。正如荣格感言,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把所有精力都倾注于研究自然,而对人的精神研究却很少,在对外界自然的探索中,人类逐渐迷失自我,被时代裹挟,被无意识吞噬……
在荣格去世60多年后,我们重读他的这本《个体成长心理学》,汲取他的睿智经验,深入到我们灵魂的居所,去探究我们的命运是如何形成的,继而关照到我们的生命情感需求,这无疑是在走一条“回家”的路。
本文作者:傅安国(海南大学国际商学院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