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痖弦于温哥华当地时间10月11日去世,享年92岁。这位从河南走出的大诗人,终其一生的创作,很多是围绕故乡和母亲的主题。2019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痖弦回忆录》,记录了诗人对自己人生和创作的回顾,浓浓的思乡之情流露在字里行间,今天我们经授权刊发书中部分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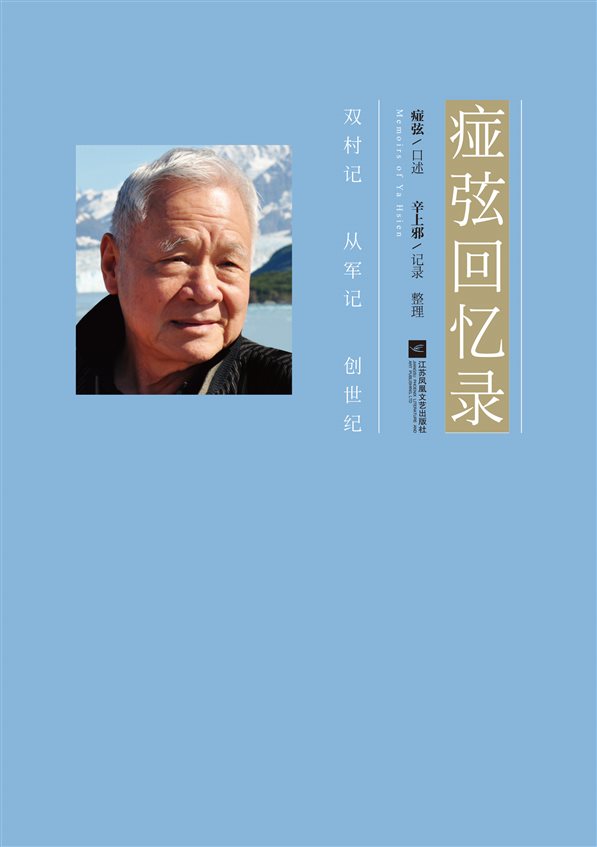
《痖弦回忆录》痖弦口述 辛上邪记录整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版/52.00元
【精彩选摘】
双村记
回忆我的故乡要从古诗《十五从军征》说起。“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诗歌描述的是:一个出征多年的人回乡,家里人都去世了。老房子还在,一片荒凉,他进去看到野兔在狗洞里跑来跑去,雉鸡在梁上飞起飞落。他到天井里煮熟了野菜,却不知道端给谁吃。我读这首诗的时候,大概十二三岁,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悲惨的事情。可是现在想一想,我还不如那个《十五从军征》的老兵啊!因为他八十还能归乡,而我却一直飘零在外。年轻时读诗,觉得是文人的夸张,哪里知道这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我离开家时十七岁了,所以对家乡的记忆非常完整。我的文学创作很多都是围绕着母亲和故乡两个主题。像我诗中的红玉米晒在房檐下、春天来了孩子们在打麦场上滚铁环,都是来自对故乡的怀念。后来我的诗歌写作中断了,我曾想过有一天我再写诗时会写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会写故乡。故乡真是一辈子写不完。而且人是越老越想家、越老越想父母。因此,一个人如果有完整的对故乡、慈母的记忆,可能够他写一辈子。当然,根据他年龄不同、艺术技巧不同,会体现出不同的风貌,可这是永不止息的主题。故乡是我永难忘怀的,如一首诗中所写,“你离家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戴着那顶破斗笠/不,那是故乡的屋顶”。现在,在我八十多岁时,我最想写的还是我的故乡回忆。
我给故乡回忆取名《双村记》——一个村子是我们家的村子,一个是我外婆家的村子,中间差十二里地。我的故乡在河南省南阳县,我从小就在这两个村子间游走,稍大才去了县城。两个村子加上南阳县城就是我对故乡的全部记忆所在。
平乐村
外婆家的村子是黄土地,我们的村子是黑土地。外婆家是明末从山西迁过来的。从山西移来的时候是一个大家族,官府就地分家——河那边是萧坡,河这边是平乐村。他们把一口铜锣断开,两半破锣分别给两边的村子,将来把两半破锣的碴口对起来,就能看出原本是一口锣,也就是一家人。要子子孙孙不忘本,永远记住是一脉所出,以后要互相帮忙。“破锣”两个字音化为萧坡的“坡”和平乐的“乐”。外婆他们在平乐村。他们村里有几家大户盖的是瓦房,形制看起来像山西的房子,青砖青瓦、五间头、四合院。我们王家祖上也是山西来的,但没有家谱,一穷二白。我们的村子就很简陋,都是草房。我妈妈为什么嫁到我们村?因为我外婆家后来渐渐穷了。我爸爸家有几亩田,娶了没落的大户小姐。外婆家的村子和我们的村子对比鲜明,一边富有文化气息,一边是蛮荒之地。
明末时河南人少,官府逼着山西民众南迁,还要有懂各行各业的,比如懂医药的,懂建筑的,读过书能识字的。他们来的时候带来了文化。我外公他们家族一直经营着药铺。我外公就是眼科大夫——在我们那里眼科医生叫“眼科先儿”——他开个药铺,也看病。我小时候就在这个药铺里跑来跑去。我外公非常想让他的子女继承衣钵。我妈妈是长女,下面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妈妈和两个姨能帮他抓药,但没学会中医。外公又希望我能继承,我小的时候他总是编故事讲这些事儿,可惜我也没有继承他的事业。
外公除了门诊,还做眼药。眼药是半流体的,有的装在高粱叶子里,乡下人叫“桃粟捆儿眼药”——家乡管高粱叫桃粟。有的也装在螺壳儿里,用蜡密封起来,还贴着药名和字号。外公也看病。他看病收费非常低廉,穷人买药就收个成本钱或者完全免费,一般的顾客就是半价。因此,他在乡里间特别受到尊敬。在我幼年的记忆中,他药铺的味道特别好闻,我在那些高与梁齐的药柜间跑来跑去。药铺里敬着泥塑的骑着老虎的药王爷孙思邈的像,一进门就能看到。药铺里有一副对联,“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横批是“杏林春暖”。
我小时候喜欢偷吃外公的甘草,甘草很甜,小孩子总是喜欢吃甜的。我想外公早就发现了,但他从来不讲。生地也可以吃,不是那么甜,也能吃。再大了,就是向外公要木通。木通不是吃,是放在墨盒里。上小学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墨盒,墨盒里有一块棉花,我们研了墨汁,或买现成的墨汁,倒在墨盒的棉花上,棉花上面要再盖一个东西,写字时笔就不会沾上棉絮。通常是去药店拿一块木通——盖木通的办法就是外公告诉我的。
乡下人管砚台叫“砚凹”,那时还是以研墨为主,墨汁还不流行,要去大的镇子上才能买到。过去中国人的诗为什么写得那么好,我想是因为写诗前麻烦事儿太多——要研墨、发笔,研墨研半天才能写诗,正好构思。发笔是说新毛笔或干硬的毛笔都要用温水发,水温不要高,也不是冷水,要慢慢把笔泡开才能用。写字要有好的环境,写字要有好的心情。这些事情都做完了,才能静下心来写。
外婆胖胖的,非常慈祥。她最喜欢我们帮她抓痒。抓的时候逗我们说:“你这娃儿,哪里不痒你抓哪里。”她还会唱各种歌谣。比如她抱着我时会唱:“抱外孙,不如抱草墩儿。”我外婆虽然平时很和善,但厉害起来也很厉害——有一年,有贼人来偷东西,给她发现了。老太太就跟他们理论,把贼骂得抱头鼠窜。
我在外婆家非常快乐。当时不晓得有“文化”这个概念,现在觉得他们家是有文化的。他们家有秩序。当时也不知道秩序是什么。反正我家那边就是赌博场,还有土匪出入。而外婆家感觉不一样。我一到平乐村就不愿意走。走的时候大人把我放到牛车上,我哭着跳下来,就是不想走。
他们大户人家的家族规矩很大,大哥就是大哥,大嫂就是大嫂,出入应对都是有一套规矩的。兄弟姐妹排行都是按照家族大排行,所以我有十三姨啊、二十表哥啊。我妈妈是老七,他们都喊她“七姨”,我大姨是老八,小姨是老九。一个管一个,秩序井然。
他们每一家都有铜器,就是锣、鼓、钹等等,要过年才打着玩儿,每家都打,好不热闹。我就是在外婆家学会了打鼓。念小学时我是鼓乐队的“要角儿”——打大鼓。
外婆家在一条大河旁边。这条河从南阳流过来,一直流向襄阳,注入汉水,是可以行船的。我们在河里游泳——家乡管游泳叫作“洗澡”——男孩子调皮,扒着去远方的船游好久。船上有使舵的女孩,跟我们笑,我们就跟着船漂。漂到激流的地方就上岸了,再跑回来。我特别喜欢这条河,一天到晚在河里玩儿,它的名字叫白河。李白曾几次经过南阳,诗歌中“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就提到了白河。
年龄稍稍大些时,我就更野了。有一次船老板和他太太大概是回娘家了,没人开船。我们一群野孩子就把这条船划走了。也去摆渡,接客人。过路的客人还真上了一船,有卖油的、挑担儿的,还有些老太太。到了河中间,我们把船用篙一定,要收钱,没有钱不开。有几个老太太骂人:“你皮吧,我认识你妈。我告诉你妈去,你就得挨揍。”听了这话,我们哪还敢要钱,赶紧开船。渡船本来是不要钱的,船夫每年收粮食。秋天打粮食时,他去码头两边的村子里挨家收粮食,给多少算多少,没粮食给点鸡蛋也行。《皇冠》杂志有个专栏叫“青春岁月”,访问过很多人,我也是其中一个被访问者。我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张爱玲看到后来信说,她读了访问记上这段场景,她觉得很苍凉。我们当时只是一味地皮,哪里知道苍凉不苍凉?张爱玲还说,“这题材太好了,你应该自己写。”
连阴雨久了,沟满河平,河上涨大水的时候,从上游冲下来很多东西,有树干、家具、牲口等等。下游的人就在河里捞东西,“发洋财”。河边的沙子都是细细的白沙,被风刮成沙岗——现在当然都被现代化建设给用掉了。孩子们喜欢从沙岗上打滚滚下来,一点都不疼。沙子也侵蚀旁边的果园。果园里的沙子越堆越高,已经接近果树枝子了。我们觉得最过瘾的是躺在树下,不用动手,只用嘴巴接着就能吃到水果,吃完了再吃另外一个。那时小孩子去果园里偷吃是可以的,一般园主基本上不管。我们就觉得痛快得不得了。桃核儿留下来,穿成串挂在脖子里辟邪——桃树是鬼的舅舅,鬼怕桃树。
因为有沙地,花生种得很多。家乡管花生叫“落花生”。花生播下去很容易生长。长到一定时期,小孩子去地里刨花生吃。用脚把花生周围的土踢松,用手把花生勾出来,将大个儿的取下,再把枝子埋进沙地,小的花生还能继续生长。收获花生时,是连着沙子一起铲起来,放到一个大的像双人床似的可以摇晃的筛子里,从两边一起摇晃,沙子就漏下去,剩下花生和花生秧子了。再把秧子和花生拿到场上,晒干了去掉秧子,留下花生。每一家都有个花生仓屋。花生堆到梁那么高。我们喜欢从高处滚下来,好不快乐。收获的花生除了自己吃,大部分都卖掉了,这是每家的重要收入。小孩子没玩具玩儿,就拿两个花生,用尖儿的部分顶,谁的破了谁输花生。那也能玩儿半天。
外公和他弟弟(我叫叔公)两家中间有口井,有条小路。井旁一年四季都有女人在洗衣服。往常洗衣服的时候,洗干净了,把衣服拿回家放在米浆或者高粱浆中上浆,然后晒。晒得半干时,放在平的石头上用棒槌捶。古诗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有人说,黑灯瞎火的,怎么能洗衣服呢,晚上妇女去河边也不安全啊?其实不是洗衣服,是捶衣服——衣服晒了一天,到了黄昏后晒干了,不用熨斗,用棒槌敲打。捶打过的衣服特别整齐,简直可以站着不倒,穿起来也体面。井里有柳条编的辘轳。夏天把瓜果用柳条篮子系到井的深处,第二天拉上来吃,这种水果叫“井畔凉”,吃起来很过瘾,像现在的冰淇淋那样。家乡的柳条去了皮,又细又白,编成器具后密不漏水,特别受欢迎。
我家里剩下的老东西是我妈妈做针线的筐子,也是柳条做的。还有就是那个捶衣服的石头,红卫兵来破“四旧”,拿它也没奈何,因为搬不动,就劫后幸存下来了。我小时候常常坐在上面,小孩子不穿衣服,凉凉的很舒服,这个印象非常深。有一年回乡,我对太太说,真想把那块石头运过来,运到加拿大来,将来百年后就枕着那块石头,那是我家的东西。我爸爸是在青海劳改营过世的。那个时候去劳改营要自带行李,所谓的行李就是家里的一床老棉被。那床带到异地的棉被就成了家的象征。很多死在劳改营的人的遗言就是“死后把我裹在我的棉被里”——用家里的棉被裹起来就是最大的心愿了。可是青海那种地方,两三千尺的海拔,天寒地冻,晚上人一断气棉被往往被拿走了。从家里带出来的老棉被就是家了,那个捶衣服的石头也让我觉得是我和已经不在了的那个家的关联。
……
【编辑推荐】
他是台湾文坛枢纽型的人物,文学组织者、编辑家、演员、海峡两岸拥趸无数的大诗人。他苦乐交加的人生故事,连通着大历史的风云记忆。他不疾不徐的叙说,平静中有波澜,幽默中有泪水,悲凉中有温热,每一句都动人心弦。静水深流中,汉字发出了奇光。在人生的高处,他,贡献了一部新的经典……
【内容简介】
全书分三个部分:双村记、从军记、创世纪。分别记录了对故乡河南南阳的记忆,参军的过程及军中生活,以及文学艺术活动中所交集的诸多名人,堪称一台湾文化圈的联络图。书中涉及到近百位两岸名人不曾为人知的故事和生动细节,既有很强的可读性,又有宝贵的史料价值。除了文化界,书中对其他各界人和事也有所涉猎,作者与一大批名人的近距离接触在书中也有呈现。作者情牵两岸,所表达的浓浓的大中国情怀令人感动,是一本沟通两岸民心的深情之作。
【作者简介】
河南人,少年离家,为了一碗红烧肉参加了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后来以天分和努力,成为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是台湾文化枢纽性、领袖级的人物。他还是一位表演艺术家,是两岸第一个在舞台上扮演孙中山的人。他长期担任联合报的重要职务,和政界、文化圈都有极深的交往。是台湾数十年文化史文学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初审:刘思怡,复审:张中江,终审:张维特)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