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前的今天,62岁的保罗·法默在卢旺达与世长辞,这位“治愈世界的人”永远离开了我们。他不仅是一位医生,一名公共卫生的实践者,更是一位用行动和思想撼动世界的斗士。他用一生诠释了“健康是一项人权”的信念,将医学的使命从手术台、实验室延伸到贫民窟,拓展至整个社会的公义。

▲保罗·法默
20岁的时候,法默就明确了“成为一名医生—人类学家”的使命,但在海地所直面的贫困与死亡,使他下定决心,专攻传染病学方向。获得哈佛大学医学和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后,他一边在波士顿教书,一边在世界各地奔走:创立“健康伙伴”组织、建诊所和医院、提供医疗服务、照顾病人、帮助当地建立起自己的医疗体系……
为什么穷人比富人更容易生病?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却贯穿了《当代瘟疫:传染病与不平等》整本书。
法默穷尽一生的理想便是去打破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医疗的双重标准,他认为,医生必须要成为穷人的自然代理人。本书系统分析了这种渗透到当代各类病症(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等)中的“不平等”及其成因,揭露其中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问题,直指健康不平等实为社会不平等的外化。不平等,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构成了我们的当代瘟疫。在专业的记录与剖析之外,他也在书中注入了更多对个体的深切关照,“所有这些章节,都讲述了在这些瘟疫的泥淖里挣扎的人的故事。”

2020年12月16日,博古睿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在授予保罗·法默2020年博古睿哲学与文化奖时,评价说:“我们很荣幸将博古睿奖授予保罗·法默医生。他改变了我们对于传染性疾病和社会不平等的看法,让我们明白在关心照料他人的同时,也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他重塑的不只是我们对何为疾病、何为健康的认知,更让我们知道健康应被视为一项人权,而我们对其有着道德和政治责任。”
这个世界上既有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有海地这样的国家,我们依然面对着各处肆虐的传染病与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在这样的环境中,法默的思想显得愈发珍贵。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部著作,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世界的顽疾,也指引着我们治愈它的方向。

下文摘编自《当代瘟疫:传染病与不平等》引言

[美]保罗·法默(Paul Farmer) 著
姚灏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978-7-5720-2433-7/C.0013
定价:11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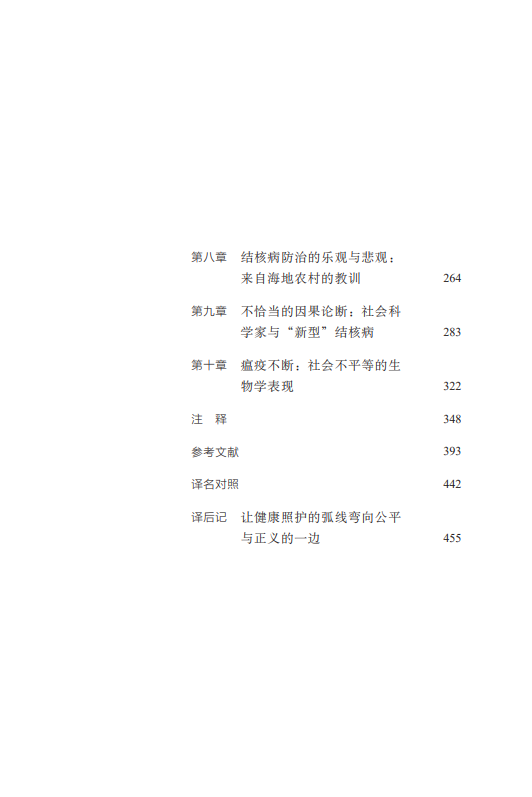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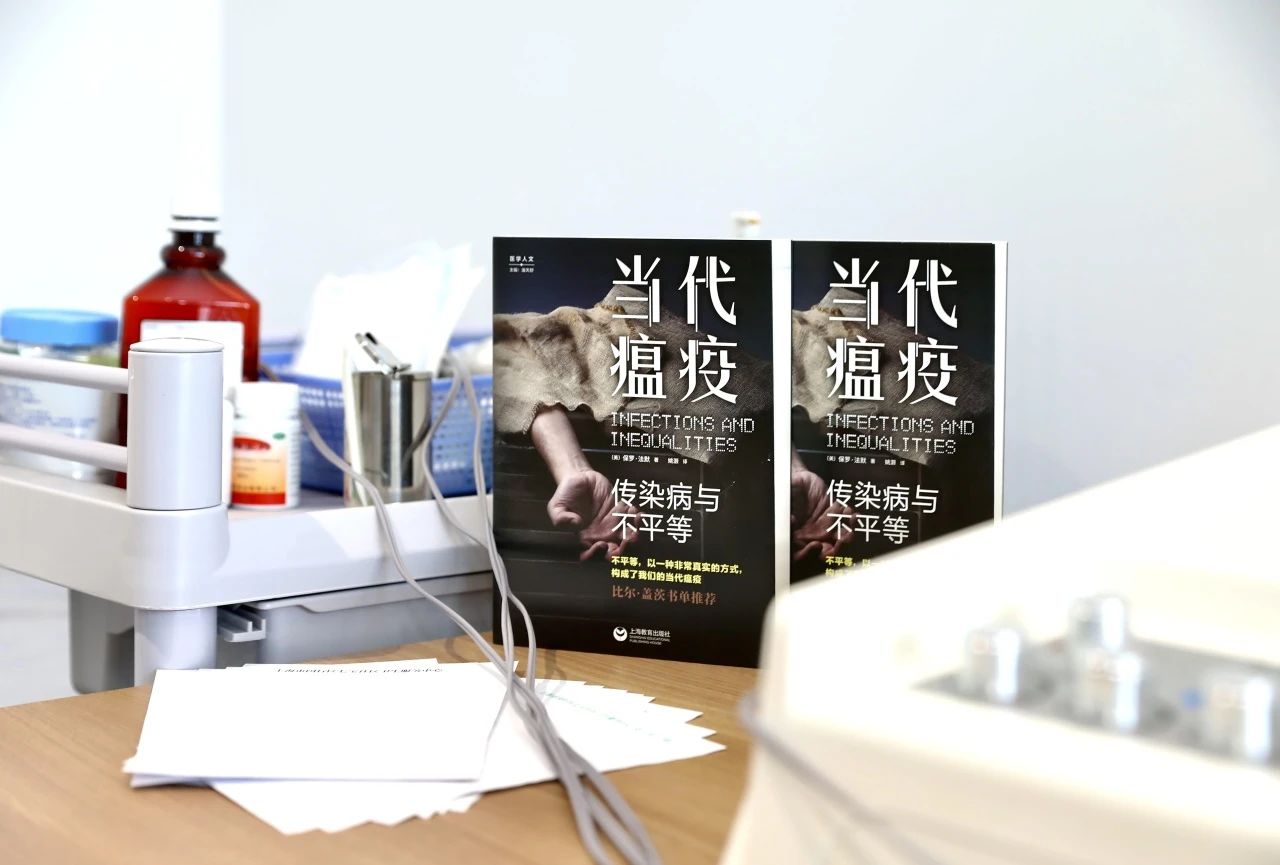
医学统计学终将成为我们的测量标准:
我们将掂量不同生命的轻重,
然后去看看到底是哪儿尸横遍野,
是在劳动者中,
还是在特权者中。
——鲁道夫·魏尔肖,1848年

是谁杀死了安妮特·让?
在她死去的那天早上,安妮特·让一切都很好,她甚至能去她家小屋不远处的一口井,拎着一大桶水回来。在那之前,她已经抱怨自己的“感冒”好几周了,可她觉得还不算太严重,虽然盗汗和纳差已让她不堪其扰。安妮特的哥哥后来回忆,那天早晨,她看起来还挺愉快、“挺正常”的。她给大家沏了咖啡,帮她妈妈给驴子驮上货物,好送往集市去卖。那是1994年10月的一个阴雨天,海地的雨季瞅着就快走到尽头。
但就在安妮特的哥哥去她家园圃后不久,这个年轻女人便突然咯起血来。一个小男孩,在院子对过,见安妮特的口中喷出一道鲜红色的血柱,然后就倒在了自家小屋的泥土地上。他连忙跑去通知安妮特的三个哥哥。他们拼了命地想叫醒她,却无济于事。只听见这个年轻女人口中发出叽叽咕咕的声响,这便是对于他们害怕的哭声的唯一回应了。仓皇中,哥哥们用床单和树枝给她搭了个担架,可即便是最近的诊所——位于他们山顶园圃下面很远处的多凯村(Do Kay),要把他们已然无法活动的妹妹送往那里,也得花上一个多小时。
半路上,雨开始倾注。陡峭的山路,变得又湿又滑,愈发拖慢了他们的速度。走了三分之二,安妮特又咳出了许多暗红色的血块,然后就不再听到她嘴里叽叽咕咕的声响了。当他们终于来到诊所时,雨下得很大。在一泊淡淡的血迹中,只见安妮特一动不动。而稍大的血块,则凝结在她被雨水浸透的衣服上,不愿融化。那一年,她才不到20岁。
当天,我也在诊所。当安妮特的哥哥同另外一个男人扛着他们担架上的“货物”冲进诊所庭院时,我正在大楼门口与一位病人攀谈。一滴滴的血从担架上流下来,滴在铺了瓷砖的庭院地面上。他们沉默着走向我,而我也同样沉默着,搭了搭这个年轻女人的脉搏。对她的诊断,简单而又无悬念,死于结核病所致的大咯血——对于她这个年纪的女人来说,几乎再肯定不过,她当时已经全身冰冷了。她的哥哥们,在一旁默不作声,不知所措,但仍以为希望还在,还有办法。所以,当我宣布安妮特的死亡时,他们一个个地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开始嚎啕大哭。
有个来自多凯村的女人,当时正在诊所里拖地,看到这一幕,也停了下来。当男人们开始哭泣的时候,她撩起围裙一角,擦了擦眼睛,便转身离去。她并不认识安妮特·让或是她的哥哥,但她见过了太多结核病人。她的妹妹,五个孩子的母亲,在1988年10月死于同样的疾病。多年后,她妹妹的孩子之一,也在结核病的并发症中死去,但在那之前,他已经因为使用某种抗结核药物而双耳失聪。

在这个时代,不应该有人死于结核
我已经见过太多结核病人了,虽然在多凯村的那个小诊所,我们只是服务于中央高原的一小片地区。但仅仅是在1993年一年,我就诊断了超过400例结核病人,这要比当年马萨诸塞州全州的登记病人总数都多。诊断结核病已经成了我的日常工作。但那天,我还是被那血、那雨,还有安妮特哥哥们的巨大悲痛,震慑到了。
但这个故事,到安妮特的悲惨结局,还未结束。我后来才知道,安妮特的一个妹妹,早年也死于结核;而几个月后,她的一个哥哥马塞林,则带着带状疱疹来到了我的诊所。他——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就像安妮特那样——此前一直在海地首都太子港做别人家的佣人。对于带状疱疹病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史往往会提示我们,马塞林很有可能是HIV的早期感染者,而此后的实验室检验也确认了这一猜想。虽然马塞林不像他的妹妹,还算比较幸运,在后来得了活动性结核后,得到了治疗,但他还是把他会死的消息告诉了他家人。
我可以说,安妮特的家人没有——也无法——理解,他们究竟为何会遭遇如此噩运。对于那样一个相亲相爱的家庭来说,失去两个原本很健康的孩子,既无法忍受,也不太公平。而后来马塞林的病也同样如此。对于他们的困惑,他们最终有了自己的假设,而后又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们觉得自己是中了巫术,是有人对他们施了咒,而这个人可能就在他们村里。
在这个村子做了十年医生以后,我已经对村民间的这种对巫术的指控见怪不怪了,我甚至花了好多年时间想理解这些指控。可相当矛盾的是,我发现,这些指控的主要功能却偏偏就是:帮助他们理解苦难。作为人类学家,我对于这样的分析十分满意。可作为一名医生,我却觉得,把可预防或可治疗的疾病归结为村民间的这些口角,实在是让人不太好受。
作为医生,我坚持认为,在这个时代,不应该有人死于结核,因为结核完全是可治愈的。但同时,结核又是这个世界上导致年轻人死亡的头号传染病。据估计,每年有300万人死于结核。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数字可能是惊人的,他们可能在报纸上看到的更多是埃博拉或是“噬肉菌”,却很少会看到结核。不管是在科研圈子里,还是在大众媒体上,结核已经不再能引起大家太多注意了,因为它影响的往往是这个世界上的穷人。而巴里·布鲁姆则把话说得更明白,他说,结核“实际上已经被我们忽视了有整整20年乃至更长时间了”。
对许多人来说,当他们听到传染病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死因时,可能会觉得非常惊讶。比如,1995年,全球估计有5200万例死亡,而其中,大约1730万例是因为细菌性、病毒性或是寄生虫感染。虽然这些死亡大多数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传染病依旧是美国穷人的主要死因。一项针对纽约福利金领取者的研究发现,在这些人中,结核和艾滋病的发病率惊人得高:在1984年登记的858名福利金领取者中,有47人最后得了结核病,84人被诊断出艾滋病。因此,这项研究也就告诉我们,对于美国穷人来说,结核和艾滋病的发病率甚至要比许多贫困国家还高,而且是美国全国发病率的70倍。实际上,单单是领取福利金以及有药物或酒精滥用史这两项,就已经和死亡有着非常强的相关性了:整整183人——是这个队列的21.3%——都在八年时间里发生了死亡,而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甚至小于50岁。

传染病与不平等
阿马蒂亚·森曾经发现,在任何有关平等的批判性论述中,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方面的平等”?这本书要论述的就是传染病分布及结局方面的不平等。这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像是安妮特·让和她兄弟姊妹那样的人容易死于传染病(比如结核、艾滋病和疟疾),而其他人则往往风险要低呢?这本书想讨论的是: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这样一些不平等,又是什么因素在维持着这些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在表面上好像是生物层面的,但它们其实主要是由社会因素所决定的。这本书还想讨论的是:我们的社会会对传染病作何种反应,是隔离检疫还是巫术指控?
这些讨论,让我能够穿梭于许多不同的关于风险与结局不平等的解释之间,包括官员们的解释与学术界的解释。我想说,关于传染性疾病的分布与病程,学者们往往会做出“因果论上的妄断”,从而弱化了他们为理解传染性疾病所能做出的贡献。这些论断之所以是妄断,是因为它们根本就是错误的,或者是存在误导性的,而且还因为它们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本可以开展合适的干预措施来治疗甚至治愈像安妮特·让这样的人。这些妄断,也同样转移了我们对于社会层面疾病的注意力,这些社会层面的疾病加剧了人们生物层面的疾病,而生物层面的疾病往往是可预防的。

本书引用了许多来自海地、美国、秘鲁等地方的数据,希望能对这些妄断加以批判。“新发传染病”领域的文献越来越多了,但我希望,《当代瘟疫:传染病与不平等》这本书,能纠正这些文献中的一些观念,并能作为一个补充。虽然许多研究传染病动力学的人都同意,新疾病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社会产物,但很少有人分析特定的社会不平等在其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然而,这样的不平等,却深刻地塑造了传染病的分布状态,而且也影响了那些患者的健康结局。
HIV也好,结核也好,甚至是埃博拉,它们的暴发都是有相当明显的模式,而且它们所导致的社会反应,也是有模式可循的。这一次次的暴发,都提醒我们,关于疾病新发的模型,必须能够动态变化,是系统性的,而且必须具有批判性,要批判性地对待那些肤浅草率的因果论断,尤其是有些因果论断忽视了社会不平等的致病性。我们的社会,人际连接越来越紧密。在这样的社会里,关于新发传染病的任何批判性论述,必须考虑到一点,那就是宏观社会作用是如何导致个体间的不平等位置的。持有“批判性的认识论”,必须找到,我们的主流分析框架究竟掩盖了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什么因素。对待这些疾病新发模型,必须能够将变化与复杂这样两个因素纳入其中,必须有全球性的眼光,同时又能充分意识到地方差异的存在。

面对这样一本批判性论著,读者不可避免地要对我的学科视野产生疑问。虽然我是一名全职的临床大夫(同时也身兼人类学家的身份),但这里的文章既不算是临床论文,也不算是民族志写作。毋宁说,它们是嵌入在医学与人类学的夹缝中,自由穿梭于这样两个不同学科以及包括知识社会学在内的其他一些学科。这样一种故意而为的“学科交叉”,绝不是为了将作者从学科责任中释放出来,而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本书要讨论的疾病风险与结局的不平等,是嵌入在复杂的生物社会现实(biosocial realities)之中的。而要想理解这样复杂的现实,必须采取一种生物社会分析范式,能够自由地旁征博引不管是临床医学还是社会理论的知识,能够将分子流行病学与历史学、民族志研究与政治经济学进行结合。当然了,要实现这样一种融会贯通,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正如芬贝格和威尔逊所说,这是流行病学的“圣杯”。
最后,这本书也是一种形式的抗议。我这里所描述的种种健康结局不平等,大部分都是社会分歧的生物学表现。我们本可以——也本应该——规避安妮特·让的死亡,而有效的规避措施也许涵盖了从临床到政治不同的向度。换言之,我的结论就是:我们需要介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要去抵抗这世间的错觉或混淆。

(内容来源:上海教育出版社)
(供稿:张丽霞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