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元年(1064),苏轼在凤翔任期满,朝廷召他返回汴梁,入判登闻鼓院。宋代官员的考核、升迁制度叫磨勘,取磨炼、勘察之意。文官磨勘三年,武官磨勘五年。
靠近年底了,凤翔连日雨夹雪,朔风千里,树木光秃秃的,全无一点绿色。秋收冬藏,而人要在大地上挪动。王弗偏又卧病,苏轼决定推迟行期。
苏轼写诗:“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
兄弟不相见,屈指一千天。弟弟想哥哥更甚,他在京城一直闲着。父亲忙着编修礼书,身子骨也大不如前了。苏轼赶赴汴梁的愿望十分强烈,妻子一病,他改变了主意。
王弗十六岁嫁给苏轼,三年后得一子苏迈,其后再未生育。她身子弱,气血不足,也许在凤翔有过身孕,流产了。她一个弱女子,性格却像程夫人。她注视着自己的丈夫,想要施加某些影响。程夫人生前可能嘱咐过她。嫁苏轼十一年,她大约九年半和丈夫在一起。
苏轼不愿走,王弗催他上路。她硬撑着身子,大口吃饭,快步行走,往脸上涂胭脂,以示肤色红润。她说病已好了,可以动身了。她连日说了好几次。她一把抱起六岁多的儿子苏迈……于是,苏轼动身。一家子的车马未到长安,雨雪更大了,道路泥泞,望不到尽头。河水结了冰。刺骨的寒风吹进咿呀作响的车厢,王弗紧紧搂着儿子,为儿子挡风。
一行人夜宿华阴县。王弗整夜咳嗽。到汴梁宜秋门附近的南园,她又躺下了,有气无力的样子。苏轼请来大夫给她瞧病。将息了半个月,王弗渐渐气色转好,却又忙起来,收拾南园的这个家,种菜喂鸡,给儿子讲书本,为丈夫洗官衣,为公公跑药铺。苏轼到登闻鼓院上班,也是忙得两头见黑。回家饭菜香啊!苏轼听到妻子哼唱欢乐的家乡小曲。其实是哼给他听,叫他放心忙公务。
五月,王弗病倒。中旬,王弗明亮的丽眼永远闭上,一头青丝进了黑棺材。高挑而鲜艳的青神姑娘,温婉贤惠的妻子,未享几天福,却忽然西去,千呼万唤唤不醒。
棺木殡于寺庙,以后归葬故里。
王弗去世后不到一年,苏洵亡,享年五十九岁。
老处士苏老泉受欧阳修的赏识,得以不仕而官,为朝廷编礼书,格外勤奋。几年累下来,积劳成疾,终于不治。他兴奋,乃至亢奋,于是勤奋,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一展平生抱负,报欧阳公知遇之恩。他连年加油干,干到油枯灯灭。
苏洵偏爱战国的纵横家,对老庄的平和冲淡察之未详。立功立言之志过于强烈,不怕费周折,不顾病且衰,执意要干出一番名堂。这类强力意志,形成了古今太多人的生存盲点,苏洵是其中之一。
孔孟一生激烈,却是懂得“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通体舒展貌)。
孔子七十三岁,孟子八十四岁,寿同庄子,逊于墨子。老子一百多岁,那神仙般的飘逸身影,提醒着炎黄子孙这一点。
短短几年间,苏轼丧母,丧妻,丧父。他才三十岁,屡遭大变故。“双料状元”仿佛身在青云之上,忽然跌进痛苦的无底深渊。他诉诸文字的不多,士大夫讳言家中事,苦难中的内心历程远在史料之外。令人惊讶的倒是苏东坡承受痛苦的能力,后来亲友们逝去,他一次次大恸,永无休止地怀念。痛苦,怀念,追思绵绵,在古代和前现代乃是人的常态。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知密州时,写下这首词,怀念妻子王弗,柔情万端,直抵永恒的无助与绝望。
苏洵既亡,士大夫吊唁者二百余人。宋英宗赐银一百两,绢一百匹,韩琦、欧阳修等大臣赠银数百两,苏东坡皆不受,他希望朝廷追赠先父为光禄寺丞,官六品。这是父亲的遗愿,又能恩荫于苏家的后代。朝廷批准了,拨一艘官船让苏氏兄弟扶棺归乡。走水路,逆流而行一千六百余里,历时三个多月。
船上两副黑漆棺材,幼小的孩子们作何感受?江水,太阳,星空,这些亘古不变之物与生命之短暂,形成强烈反差。苏轼奔丧、扶棺,未留下一首诗。对死亡的追问显然是儒学的短板,“未知生,焉知死?”先秦诸子的死亡追问被孔夫子遮蔽了。
江行百余日,苏轼每天面对父亲和爱妻的亡灵,他在想些什么呢?
人在何处?人在生与死之间。静静的黑夜里,黑棺材显得很大……
治平三年(1066),苏氏兄弟回到眉山丁父忧。
苏轼葬父亲和妻子于眉山城之东,今天的土地乡苏坟山。苏洵、程氏、王弗均葬于此,青山绕陵墓,万松伴英灵。苏轼丁忧近三年,手栽松苗三万棵。兄弟二人带着年幼的孩子常常待在那儿,躬身栽树培土,仰看蓝天白云。
我曾经多次拜谒苏坟山,那地方太美了。隐约似有气场弥漫于周遭。我起初以为是个人感受,问别人,竟有同感!
王弗墓前的清风如泣如诉,仿佛诉说着她的幽怨:她与苏轼,欢娱太少了。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太快,十年一晃而过。苏轼说过的,要和她生同衾死同穴,可他的陵墓远在河南郏县……
王弗频繁地走进苏轼的梦中,似乎要补上夫妻恩爱的好时光。苏轼细腻回应她,爱不够怜不够。又是一个十年,阴阳时向梦里缠绕,然而梦要醒,美满的梦境会突然中断。诗人深陷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中。
熙宁八年(1075),知密州的苏轼写下《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阴阳隔天地,相爱至深的男女永无消息。这是人类永恒的绝望之一。想念亡人越深切,越能“触摸”到这种绝望。
苏轼对王弗的怀念,是不知不觉的、倏然而至的—这更接近怀念的本质。他事先并无计划,要在亡妻的十年忌为她写点什么。伟大的艺术作品好像都跟意志没关系。感觉是慢慢积聚,自发地寻找它们的喷发点:这个谜一般的漫长过程也许正是艺术吸引人的奥秘所在。诗人提纯了普通人的深切感受。《江城子》语句平实,对应日常生活的场景,七十个字,说尽无穷思念。浓郁的哀伤托出王弗凄婉而美丽的形象。汉语的表达能力真是令人一再惊奇。
而眼下有一种喧嚣:读图时代到来了!我不知道这是鼓吹进步还是提倡退化。我只知道,这首简短的悼亡之作,明显胜过那些类似题材的、哪怕是较为成功的影视剧。影视剧通常看过就忘了,而要忘记“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的文字,可能需要用点力气。
苏轼这首《江城子》,自它问世至今,打动过多少人,没人统计过。肯定是天文数字。没有比这更哀婉的声音了。我想到一个“右派”的故事,不妨在这儿讲一讲。“右派”是成都人,当然是知识分子,由于乱说话,1957年被下放到眉山尚义公社,接受改造。此人姓陈,我的一个知青朋友徐文钦曾是他的邻居,尊称他老陈,常去借书或讨教书法、小提琴指法。老陈的妻子不是“右派”,却随丈夫到了尚义公社某生产队,过着艰辛而屈辱的日子。她随时可以回成都,可她不走,她守着丈夫吃苦。这一守就是八年。八年之后她踏上了黄泉路,葬于异地他乡,轮到丈夫来守她了。年年忌日,老陈到她的坟前献一束花,念一遍“十年生死两茫茫”,双泪长流……类似的故事肯定很多很多,九百多年来,苏轼的这首悼亡经典打动过无数的中国人,催泪如江河。
而读者掉下的眼泪,乃是人世间最为深沉的眼泪,和那些煽情煽出来的液体不可同日而语。
煽情的特征是:让眼泪来去匆匆、莫名其妙,它本身拒绝深沉的感动。因为一旦深沉,情感持续的时间长,它就不好卖钱了。煽情的目的是:让你哭,是为了掏你的腰包。一切以煽情为职业者,都是人类情感的小偷,他们打着文化产业化的旗号,把感动从人的内心深处生生剥离,推向易于调动、易于变花样耍花招的浅表层。
本文摘自《苏东坡传:诗酒趁年华,烟雨任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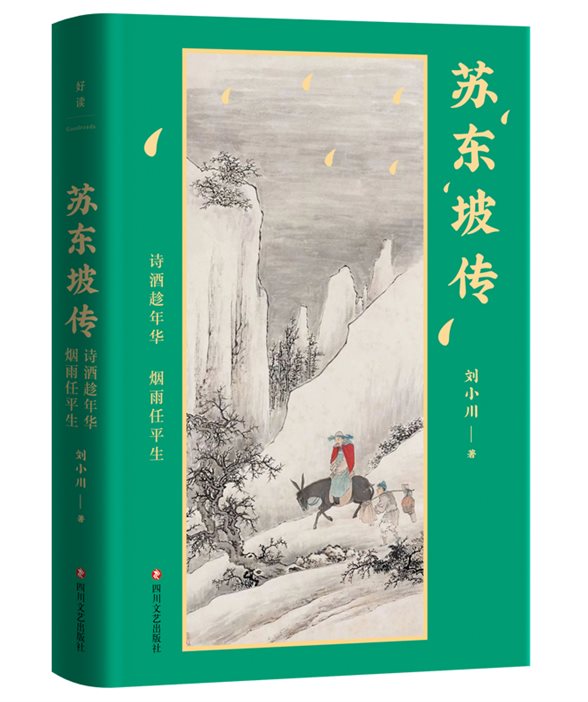
《苏东坡传:诗酒趁年华,烟雨任平生》刘小川著/好读文化策划、四川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版/55.00元
ISBN:978-7-5411-6557-3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